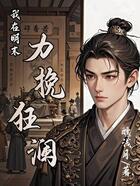
第123章 叁臣衍圣公
崇祯十七年七月初一,兖州东关外人声鼎沸。
蟒袍乌纱的官员们聚集在城门两侧,神色各异。持枪执刀的兵士严阵以待,刀枪寒光闪烁,戒备森严。
“史部堂来了!”人群中突然响起一阵骚动。
只见史可法迈着稳健的步伐走来,一身青色官服,面带微笑,与周围官员点头致意。
“这阵仗,迎的是哪位?莫非是圣上驾到?”一名穿着绸缎的商人小声问身边的伙计。
“不可能,若是圣上亲临,早就该出城三十里迎接了。”伙计压低声音回答。
“那会是哪位阁老?”商人继续追问。
一名身着武将服饰的中年人听到议论,转过头来,嘴角带着几分嘲讽:“诸位猜错了,今日是迎接曲阜孔家衍圣公。”
“衍圣公?”商人一愣,“他不是已经投了清廷吗?”
“可不是么。”武将冷笑一声,“这都换了三次主子了。先是投了李自成,后又归顺清廷,如今又要来见咱们大明的官员。这变化比天气还快。”
史可法站在城门前,眉头微皱。阳光下,他的面容显得有些疲惫。
他心中清楚,这位衍圣公的来意并不单纯。自从海州行在下令没收孔家在登莱的田庄后,这位向来善于见风使舵的衍圣公坐不住了。
几万亩良田,说没就没。这可比流寇和鞑子来袭还要吓人。
史可法望着远处尘土飞扬的车队,暗自思量。孔家在山东根基深厚,光是祭田就有数十万亩,更别提这些年通过各种手段侵吞的土地了。
“大人。”一名幕僚凑到史可法身边,“衍圣公此来,恐怕是为了田产的事。”
史可法轻轻点头:“我知道。”
“那大人准备如何应对?”幕僚小心翼翼地问。
史可法没有回答,只是继续望着远处。幕僚见状,识趣地退到一旁。
一个时辰后,车队终于抵达城门。十几辆马车停在城门外,护卫们纷纷下马,列队两侧。
孔胤植从中间的马车上下来,一身华贵的衣袍,举止从容。他的目光在四周扫视一圈,最后落在史可法身上。
“下官见过史部堂。”他拱手行礼,面带谦和的笑意。
史可法还礼道:“衍圣公远道而来,辛苦了。”
两人寒暄几句,便一同入城。沿途百姓纷纷驻足观望,有人指指点点,窃窃私语。
“这就是孔家的衍圣公?”
“听说他投了清廷。”
“嘘,小声点。”
孔胤植似乎没有听到这些议论,依旧保持着优雅的姿态。只是他的手指不经意地捏紧了衣袖。
他也不想来啊,可是昨日听管家来报,朝廷已经派人去登莱丈量田亩,听说还要查看当年的账册。这些哪里经得起查呢?就连曲阜的祭田都不一定能保得住。祭田,那可是孔家的根基。历朝历代都不敢动的东西,可这太子不讲武德......
他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路上,孔胤植状似无意地说道:“听闻朝廷近来在整顿田亩,下官深感欣慰。只是山东民生艰难,还望朝廷三思。”
民生艰难?史可法心中冷笑。这位衍圣公,果然是为了田产而来。
“衍圣公说得是。”他不动声色地应道,“朝廷一切施政,自然以安民为本。”
孔胤植暗自观察史可法的神色,见对方不露破绽,也不好再说什么。
一行人来到驿馆,宾主分主次落座。茶水上来,香气袅袅。
“衍圣公此来,不知有何要事?”史可法开门见山地问。
孔胤植放下茶杯,沉吟片刻,说道:“下官此来,是为表忠心。”
“哦?”史可法挑眉,“衍圣公的忠心,是对大明,还是对大清?”
这话说得不客气,但孔胤植却不恼。他叹了口气,说道:“乱世之中,人人都想保全性命。下官一时糊涂,确实有负朝廷。但如今太子殿下励精图治,下官愿重归大明,以赎前过。”
史可法不置可否。他很清楚,若不是朝廷动了孔家的田产,这位衍圣公是不会这么快改弦易张的。
“衍圣公既有此心,本官自当转达。”史可法说道,“不过眼下山东形势复杂,还望衍圣公谨言慎行。”
孔胤植连连点头:“下官明白。”
这位衍圣公,确实是个人物。从大顺到大清,再到大明,短短几个月就换了三次门庭,当真是有辱孔子名讳。若不是有这个世袭罔替的头衔挡着,哪还能毫发无伤甚至是风光如旧。
而此时的朱慈烺正坐在海州抚军大元帅府内,手中把玩着一枚玉质印章。等待着召见登莱二府的举人和秀才。
“殿下,登莱二府的举人和秀才已经在外候着了。”李岩躬身禀报。
朱慈烺放下印章。“让他们进来吧。”
这场恩科考试,表面上是为了选拔人才,实则暗藏玄机。李岩给他出的这个主意,可谓是一箭三雕。既能摸清登莱二府各地大户的底细,又能借此拉拢他们组建团练,还能让这些人主动配合整顿地方。
“高密县才子张伯任求见!”
随着通报声响起,一个风度翩翩的年轻人阔步走入大堂。他身着玉色生员服,头戴方巾,面如冠玉,目若朗星。举手投足间,带着几分书生意气。
“学生张伯任,拜见太子殿下!”张伯任跪地叩首,动作标准,显然是经过精心练习的。
朱慈烺打量着眼前这位高密县的头号才子。锦衣卫早已查明,张家在高密拥有数万亩良田,佃户过千。这样的家族,正是他需要拉拢的对象。
“免礼平身。”朱慈烺和颜悦色道,“听闻你的策论写得极好,颇有见地啊。”
张伯任闻言一愣,眉头微不可察地皱了皱。他清楚记得自己那篇文章写得并不出彩,考题太过刁钻,就连他爹这个举人老爷看过后都直摇头。
“殿下谬赞了,学生水平真是有限,文章实在平平无奇。”张伯任谦逊道。
“不必过谦,你说得很对,持久战确实需要稳固的后方。”朱慈烺继续夸赞道,目光却在观察着张伯任的反应。
张伯任越发困惑,他记得自己根本没写到这些内容。难道是记错了?还是说...这场考试另有玄机?莫非是有人换了他的卷子?他心中疑窦丛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