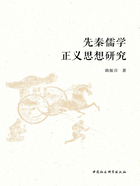
二 思想与方法
我们在研究思想进程时,首先,要把思想放入历史框架之中进行理解和阐释。其次,要把握联结历史与思想关键要素的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形式的发展点。这些关键要素的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形式的发展点不仅是历史过程的真实内容,也是思想进程的逻辑环节,更是我们得以进入历史,理解思想的门径。正是由于人为的、主动的精神因素的注入,才使得整个宇宙演化实现了从自然过程到历史进程的跃迁,而文字、语言与逻辑正是由自然过程与历史进程交错扭合、相互碰撞而结出的精神文明之花,是考察历史进程与思想进程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形式的发展点。文字的产生首先是为了指示具体事物,而语言则是要表述不同事物之间的客观联系,逻辑则是要在诸种事物之间的关系之上寻找一个统一的、终极的理论解释。文字→语言→逻辑的文明演进范式不但表明了人类认识能力和思维能力的发展规律,同时也表明了人类社会物质活动普遍化范围的不断扩大和精神生活抽象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正义需要尊重不同的个性和公平合理地对待每一个人,但这种尊重和对待不是各持己见、你死我活,而是要在相互商谈求同存异基础上取得共识。也就是说,正义既具有基于个体差异的个别性,也具有群体交互性和一般普遍性。这和文字→语言→逻辑的文明演进范式相统一,也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和演化趋势相一致。
(一)文字
尽管语言的发展先于文字产生是人类社会演化的客观历史事实,但正是由于文字的产生才不但使得语言的发展开始步入成熟化和规范化的历史轨道,而且使人类历史更为详尽的记述和更为有效的传承有了全新的载体和工具。文字一经产生,就承担了指示事物、表达意义、思考问题、交流思想、记载历史、传承文化的全部功能。对于西方表音文字而言,这种文化特性或许并不显明,而对于中国之表意文字来说,文字的这种文化特性则展现得淋漓尽致。于省吾在《甲骨文字释林·序》中说:“中国文字的某些象形字和会意字,往往形象地反映古代社会活动的世界情况,文字本身也是珍贵的史料。”马叙伦也说:“要了解到文字的来源、构成等,实在是文化的一部分的研究。”[42] 唐兰在《古文字学导论》中也指出:“纯粹形声字的形母,可以指示我们社会的进化。因为畜牧业的发达,所以牛羊犬豕等部的字特别多,因为农业的发达,有艸木来禾等部,因为石器时代变成铜铁器时代,所以有玉石金等部,因为思想的进步,所以有言心等部。”与于、马、唐三位先生相比,沈兼士走得更远,在《研究文字学“形”和“义”的几个方法》一文中,他专门写了《中国文字之史学研究》一节,指出: “应用象形、会意两原则的文字,大都直接地或间接地传示古代道德、风俗、服饰、器物……等的印象到现代人心目中,简直说它是最古的史,也不为错。”
许嘉璐引黄季刚《文字声韵训诂笔记·训诂概述》云:“小学家之训诂与经学家之训诂不同。盖小学家之说字,往往将一切义包括无遗;而经学家之解文,则只能取字义之一部分。”“小学之训诂贵圆,而经学之训诂贵专。”[43] 此殆小学家与经学家之一大区别,然经学大家应以小学为基本工夫,舍此则必入不可知之途。此论虽由训诂而发,但就中国传统学术而言,则具有普遍意义。1936年沈兼士写了《鬼字原始意义之试探》一文,陈寅恪致函沈氏曰:“依照今日训诂学之标准,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44] 在其特殊语境之中,陈氏所说“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固然不能说是普遍的文化事实,然而其论却有一定的历史根据,对于中国文字的特殊性而言尤其如此。故而有不少人也试图通过对文字的探究来解释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正义思想,如石永之从“义”字的“基本义、假借义、引申义的演变及先秦儒家对义的阐释来看儒家正义思想的形成”。并断言说:“荀子首先使用 ‘正义’ 一词,把义落实到社会制度层面,以正义思想作为建构社会制度的基础,基本形成了儒家正义思想。”[45] 石永之实际上是把“义”看作可以和西方的正义概念可以互相诠释的核心范畴,并试图通过对“义”与“仁”、“义”与“礼”、“义”与“智”的相互联结与彼此关照来对中国古代正义思想作出解释。就诠释方法而言,石永之和黄玉顺是比较接近的,他们得出的结论也十分相似。明显的区别是石永之更注重文字意义上的文献学梳理,更偏重于传统学术的严谨,而黄玉顺更注重理论意义上的系统化表达,更富于西方理论思维的特征。在中国古代正义思想的研究上,石永之、黄玉顺不无同调,与他们所采用的方法类似的还有刘宝才、马菊霞等。[46] 也有一些学者试图从中国传统固有的与“义”有关的几个概念如“正”“直”“中”等来论述正义思想[47],成中英亦认为中国传统正义观可从儒家经典中的“正”“义”“直”“中”四个字得到解释[48]。但毫无疑问,他们都认为“义”字是代表中国传统正义思想的核心范畴。文字学的方法固然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不能像焦金波解释“政”“正”“王”字那样走极端。[49] 文字由于语言发展的要求而产生,亦为记录语言表达思想传承文化而服务。我们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和社会文化事实就文字而论文字,而要把对文字的理解放入整个语言发展和思想框架之中。与文字变迁相为表里的一个内容就是语言的演化,或者从根本上来讲,语言的演化是文字迁变的内在动力与决定因素。恰如陈氏所言,“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这里的“解释”一词是很值得我们再三玩味的,而解释的功能只有语言才能承担。
(二)语言
“历史研究的本质是把已经逝入历史深处的东西唤回到我们之中,使之重现于历史思维、历史知觉。然而,历史研究的过程正与历史运动的方向相反。就是说,历史研究可以说是 ‘溯洄从之’,即根据历史线索——比如说经典文献及其注疏—— ‘逆向’ 进入历史。”[50] 尽管亚里士多德说,言语是心灵过程的符号和表征,正如所有的人并不是具有同一的文字记号一样,所有人也并不是具有相同的说话声音,但这些言语和文字所直接意指的心灵过程则对一切人都是一样的。[51] 但就古代历史文化研究而言,“实际上,我们只能根据历史文献、考古材料和民族志资料,由近及远研究历史;就像依据《说文》和青铜器铭文解读甲骨文,根据《广韵》和《切韵》拟定上古音一样,思想史研究不能不以各种注、解、疏、传为线索和津梁进入古代思想世界,并通过持续的阐释活动不断激活传统”[52]。而实际情况是,单凭语言文字的记载和考古材料的解读我们并不能真正切入传统思想的内在脉络之中。这是因为,首先,语言具有模糊性和概然性,语言表述事物的过程本身就存在信息失真的诸多可能,而我们对文本的解读也会由于不同个体各个不同的心理结构、文化倾向、精神追求、价值标准、情绪状况或其他生理与心理因素的影响而导致个体理解与文本本身之间细微间隙乃至巨大差别,这也就是周易所说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周易·系辞上》)。其次,考古发现可视为一种无声的历史言说,但一般来说,除直接的出土文献之外,其他的考古材料受特定历史时期科学方法与技术手段所限,可能具有巨大解释空间的可填充性与无限人文内涵的可赋予性而只能作为对思想研究的一种间接佐证。究其原因,乃是由于时间的区隔和空间的限制而使人对事物不论是理性认识还是主观言说都可能与客观事物本身存在或多或少的不一致甚至是严重的扭曲和变形。再次,“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金刚经》)。语言只能表述具象,而对那些不可言说的深藏具象背后的事物来说语言是无能为力的,而宇宙无限运动永无止息的本性又使得在大化流行之中所有可视可见可听可闻的具象相对于永恒运动的宇宙而言又都是偶然的、暂时的、生灭的、变幻的。最后,要想把握变动不居的具象背后相对而言更为稳定的东西就必须超越具体语言表述的限制。
在谈到逻辑的研究方法时,恩格斯说:“……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不过是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53] 形式和偶然性都是个别的、特殊的、殊相性的东西,而一旦摆脱了形式的局限和偶然性的区隔就达到了一般、普遍和共相性的实在。恩格斯认为逻辑的研究方法虽然也只是“历史的研究方法”,但却能透过“历史的形式”,排除“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把握历史与思想的一般本性和普遍本质。首先,恩格斯强调了思想研究和历史研究的一致性,也就是思想和历史的一致性。其次,刨除翻译是否准确这一纯粹外部因素的影响,根据现在的语言习惯把这里容易引起歧义的定语“历史的”翻译为表述动态和强调过程的状语“历史地”或许更能贴近作者的本意。最后,恩格斯的论断也表明了逻辑的方法是准确把握思想进程的唯一方法。列宁也说:“逻辑不是关于思维的外在形式的学说,而是关于‘一切物质的、自然的和精神的事物’ 的发展规律的学说,即关于世界的全部具体内容及对它的认识的发展规律的学说。换句话说,逻辑是对世界的认识的历史的总计、总和、结论。”[54] 在这里,列宁所说的逻辑是关于“‘一切物质的、自然的和精神的事物’ 的发展规律”,“即关于世界的全部具体内容及对它的发展规律的学说”,“是对世界的认识的历史的总计、总和、结论”,实际上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之后所达到的一般的、普遍的规律性与真理性认识。也就是说,运用逻辑的研究方法可以穿透语言文字的表象而直接抵达历史与思想的深处。
(三)逻辑
近年来,黄玉顺的研究展示了中国学人努力建构中国正义理论的致思方向。毫无疑问,他由于运用逻辑研究的方式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框架。黄玉顺认为:“中国正义论的总体架构是:仁→利→智→义→知→礼→乐。中国正义论的主题是礼的 ‘损益’ 问题,即是由仁爱中的差等之爱所导源的利益冲突问题。然而同是仁爱中的由推扩而溥博的一体之仁却正是解决利益冲突问题的保证,即保证对他者私利、群体公利的尊重。这里存在两条正义原则:正当性原则(公正性准则、公平性准则);适宜性原则(地宜性准则、时宜性准则)。正义原则其实是正义感的自觉的理论表达,而正义感则是在当下生活中获得的一种直觉的智慧或良知。根据正义原则来进行制度规范的建构,还需要理智或理性。正义的最终目标不仅是礼,而是礼乐,即差异和谐。”[55]在这种理论视野的关照之下,黄玉顺还对孟子的正义思想进行了系统性的解读。黄玉顺致力于构建中国正义理论体系的努力方向是值得肯定的,但他对于一些理论核心的处理还有些粗糙和僵硬,而且过于个人化的理论建构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人们对正义思想的普遍理解和广泛接受。
相较而言,郭齐勇则由于更多地借助了西方现有的理论资源而使其对正义思想的解读显得更为清晰和明确。在《再论儒家政治哲学及其正义论》中,他以亚里士多德和罗尔斯为理论切入点,借助“应得”“配得”“机会公平”“最不利者”“实质正义”“合法性”“权力分配与制衡”“社会自治”“言路开放”等诸多西方现代政治哲学范畴,结合“天”“天命”“天道”中国传统固有话语系统展开深入讨论,并得出了“儒家的 ‘道德的政治’就是要坚守政治的应然与正当性”和“儒家正义论的最有特点的内涵,乃实质的正义”这一结论。这种组织材料,展开讨论的方法因为其逻辑的明晰性而有助于人们对正义思想的广泛接受和普遍化理解。惜乎受文章篇幅所限,郭文虽未能对中国传统社会正义思想进行更为详尽和深入的讨论,但这种中西互释或者说更倾向于以中释西的研究方法是很值得肯定、继承和发扬光大的。
一般来说,重大社会事件或关键历史进程对原有认识方式或世界图景的颠覆是进行文化反思与价值重构的发生学前提,而这种文化反思与价值重构又往往要先在地依托一个比原先更为宏阔的历史文化背景来进行,文化反思的核心就是要对生命个体和整个人类从存在和价值两个方面上的意义进行反复拷问和不断追寻。也就是说,新的历史文化背景的理论建构是进行哲学反思的逻辑前提,这种历史文化背景的建构首先涉及人在世界乃至在宇宙中的位置问题,这个问题说到底也就是人精神性的自我认知和自我建构的问题。黑格尔说,当自我认识到它自己就是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是它自己时,自我就成了精神。认识这一点对我们理解正义非常重要,因为“抽象的个别性只有从那个与它相对立的定在中抽象出来,才能实现它的概念——它的形式规定、纯粹的自为存在、不依赖于直接定在的独立性、一切相对性的扬弃。须知为了真正克服这种定在,抽象的个别性就应该把它观念化,而这只有普遍性才有可能做到”[56]。从认识发展而言,摆脱个别性,实现普遍性从而达到概念的明晰化和具体化是从经验性认识(感性认识)迈向真理性认识(理性认识)的枢纽与桥梁;从境界提升而言,以理灭欲破私立公,从个人情山欲海中跋涉出来,与普罗大众风雨同舟休戚与共是突破“肉的自我”与“小的自我”向“灵的自我”与“大的自我”迈进的重要环节。同样,正义也正是由于超越了社会正义所依存的具体社会情境而获得了趋于终极的、普遍性的和超越性的意义,“它既体现了人类智慧和思维的高度,又可以为现实中变动不居的万事万物提供一个形而上的支撑点。这个支撑点,往往蕴藏着人类的理想和智慧,是人类文明的精华所在”[57]。因此,要想充分认识和深入理解正义思想,就不仅需要高举远慕的心态和深思明辨的理性,还要有体会真切的情感、执着专注的意志和洒脱通达的境界[58]。韩愈有诗云:“我愿生两翼,捕逐出八荒。精神忽交通,百怪入我肠。刺手拨鲸牙,举瓢酌天浆。腾身跨汗漫,不著织女襄。”(《调张籍》)同样,我们对古人的理解也不能仅仅局限于文字和语言所表述的具象之上,我们不但要穿越文字和语言的局限,用思想本身的逻辑来把握义理,甚至要通过精神驰翱今古、呼啸六合、洞悉幽明的无限性来直达历史深处的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