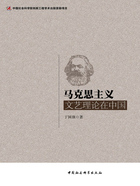
二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接受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美学)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从一开始就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实践直接相关,并始终与这种实践纠缠在一起,受其影响与推动。因而,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政治的关系,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重要特征。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认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可以被中国人接受,并最终在这块土地上生根开花,与中国人对这种理论的需求是分不开的。“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8]其实,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就在寻找这个理论。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从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再到“五四运动”,在艰苦探索与寻求中,中国人才最终找到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一旦传入中国,便成为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理论工具。
作为马克思主义有机组成部分之一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对于文学倾向性、文学党性、文学阶级性等的重视,对渴望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中国人民而言,无疑是一剂天赐良药。今天以回溯的视角来看,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产生发展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最终形成、巩固与发展是一致的。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形成以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标志,其巩固与发展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一直延续至“文化大革命”结束。虽然,这中间经历了一些曲折与斗争,但毛泽东美学的影响与地位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这其中既有中国客观的历史原因,也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自身传承关系所起的作用。中国学者杜书瀛认为,“毛泽东当然也像全世界的共产党人一样再三声称自己学马克思,但就文艺思想而言,其基本精神和关键之点却是学列宁而主要不是学马克思恩格斯”[19]。杜先生的这一看法是准确的,因为马恩的美学思想核心主要是现实主义,而列宁所强调的主要是“党的文学”的原则,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强调的文艺原则与列宁是一致的。另外,毛泽东对列宁“政党”美学的继承,经过了瞿秋白这一中介。1920年,瞿秋白去苏联访问两三年,并在苏联加入共产党,还两次见到列宁并与之合影,深得列宁文艺思想之真传。30年代初,瞿秋白在苏区主管文化工作时,又将其思想付诸实践,提出了“话剧要大众化、通俗化,要采取多种形式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这成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先声。
当然,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形成,除列宁的影响外,还与列宁之后苏联共产党的一系列关于文艺问题的决议和文件,以及苏联共产党美学家的文艺思想密切相关,因为这些因素直接影响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文艺观念。与列宁相比,毛泽东更强调文艺的“服从”与“从属”地位,更强调文艺必须“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必须“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毛泽东还提出了“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20]的文艺批评标准。1942年10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时,当时的中央总学委在学习通知中认为:(《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的事业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毛泽东同志用通俗语言所写成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此文件绝不是单纯的文艺理论问题,而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的具体化,是每个共产党员对待任何事物应具有的阶级立场,与解决任何问题应具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典型示范。”[21]由此来看,《讲话》虽然是一个关于文艺问题的论著,但实际上也可以被看成是一个重要的党的纲领性文件。在抗战时期,广大的文艺工作者按照《讲话》的精神,坚持文艺为人民大众、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走向农村,深入抗战第一线,创作出了一大批适应抗战需要、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的优秀文艺作品。
但由于过分强调文艺的政治标准,加上新中国成立以后,主流意识形态又把“人民民主专政”思想不知不觉地渗透进了《讲话》美学思想与文艺实践中去,从而给我国文学艺术事业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以及“文化大革命”十年,政治主导下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建设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美学)发展的基本状况。这种状况不仅体现在毛泽东撰写或改定的许多“按语”“社论”和文件中,同时也体现在党的其他领导人的发言,以及当时文化界的领导,特别是周扬等人的文艺思想中。其具体表现就是50年代出现了诸如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萧也牧等的创作的批判,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和胡适的批判,对胡风集团的批判,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批判等。由于政治权力的介入,这些文艺问题都成了“政治问题”。理论工作者遭到了严厉的批判和清洗,敢于坦陈直言的知识分子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左”的文艺路线因此得以大行其道。
1966年2月,江青等四人召开了所谓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并整理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简称《纪要》),将“极左”文艺思潮推向了高潮。《纪要》提出了“文艺黑线专政”论,彻底否定了新中国成立后文艺界的工作。《纪要》总结概括了新中国成立后“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的具体表现,并将之归纳为“黑八论”,即“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以及电影界的“离经叛道”论,使正确的文艺观点、正常的文艺探讨遭到了严厉批判与打击。同时,与《纪要》提出“文艺黑线专政”论的“破”相对应,“三突出”的创作原则开始成为“极左”路线指导文艺的重要准则。“三突出”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1968年5月23日《文汇报》上于会泳发表的《让文艺舞台永远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一文中,1969年姚文元将它改定为“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中心人物”,并且把它上升为“无产阶级文艺创作必须遵循的一条原则”。[22]1972年,“四人帮”又把“三突出”拔高成“无产阶级文艺创作的根本原则”“进行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必须遵循的坚定不移的原则”,是“实践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这一社会主义文艺根本任务的有力保证”。[23]“三突出”的原则和方法是违背马克思主义文艺“典型”理论的,它的贯彻必然导致文艺创作和文艺演出严重的公式化、模式化。“文化大革命”十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立场、方法、基本传统已荡然无存,思想理论界陷入深重的灾难之中。
新时期以后,经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引领下重新活跃起来。人们开始重视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等理论问题,同时为了探索文艺学美学新的研究方法,还引发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方法论”的热烈讨论。虽然“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仍然是中国学者关注的重要话题,但这时,学术研究的政治气氛已经非常宽松。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论,最终由中央高层做出决定,不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口号,而改为提倡“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社论还指出:“作为学术问题,如何科学地解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人们完全可以自由展开讨论。作为政策,党要求文艺事业不要脱离政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但并不要求一切文艺作品只能反映一定的政治斗争,只能为一定的政治斗争服务。”“二为”方针的提出及一系列文艺新政策的出台,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理论)研究走上正常的学术轨道铺平了道路。
进入新时期以后,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美学)有两次比较大的讨论:一次是关于“手稿”问题的讨论,一次是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不是“有体系”的讨论。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之后,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本身的反思,也成为当时思想界反思的重要内容,这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24]就顺理成章地被纳入到了理论研究的视野之内,对《手稿》中“人性”“人道主义”等人学思想的研究与讨论,关于“美的规律”问题,以及《手稿》本身是不是马克思的成熟作品等,都成为当时理论界讨论的热点。“异化劳动”“感性”“人的本质力量”“对象性”“自由”等这些关乎马克思对美的理解的重要概念,也都在此时得到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对马克思早期思想的研究几乎吸引了当时所有理论工作者的研究热情,仅1979年至1980年就有近百篇讨论文章,朱光潜、蔡仪、李泽厚、蒋孔阳等美学家都参与了这场讨论。80年代对《手稿》的阅读和讨论,是前所未有的,全方位、多层次的,讨论丰富了中国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新认识,使人们看到了马克思思想中众多过去被忽视的方面。
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有无体系[25]的讨论中,讨论各方均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中寻找答案,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去阐述观点,使过去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许多似非而是、似是而非的问题得以澄清,这是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引入我国以来从未有过的一次最集中、最广泛的专题性的整体讨论。这场讨论从1980年持续到1986年,前后达6年之久。争论吸引了当时许多文艺理论家,讨论的问题又几乎涉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所有方面。这场讨论是学术界开展的一次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全面学习,让人们走出了“极左”思想路线,从而更加完整准确地理解马恩等经典作家对于艺术、审美问题的基本观点。
以上两场讨论,对“后文革”时代我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理论)的起步与发展,有着极强的历史意义与理论价值。在走出极“左”文艺思潮的基础上,新时期以后直到20世纪末,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理论)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产生了一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新成果。如陆梅林、程代熙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吴元迈的“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艺术观”研究,钱中文、童庆炳的“审美意识形态论”研究,王元骧的“审美反映论”研究,何国瑞的“艺术生产论”研究,李益荪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社会学原理研究”,邢煦寰的“艺术掌握论”研究,谭好哲的“文艺与意识形态”研究,董学文的“文艺学当代形态论”研究,陆贵山的“宏观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冯宪光、马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研究,等等。这些研究涉及文艺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文艺的本质、文艺的审美属性、艺术与政治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以及艺术反映论、艺术本体论、艺术价值论、艺术主体性、艺术功用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中的根本问题,大大提升了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研究的水平与实力。
2000年以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美学)“中国化”成为理论界提出的主要任务。这一任务的提出,既与中国经济长期持续的发展相关,也是中外学术交流不断增强的必然结果。同时,作为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意识形态的国家,这也是中国美学家们试图寻求理论研究突破的一种现实选择。然而,这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国学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今后的发展目前尚处于探索之中。
如果要做一个小结,论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美学)在中国的发展大体分为这样三个阶段:一是生根发芽阶段,二是开花结果阶段,三是走向成熟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以《延安》讲话和“文化大革命”结束为桥梁与联结点。也就是说,《讲话》以前是第一阶段,《讲话》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为第二阶段,“文化大革命”以后为第三阶段。在第一阶段中,马克思主义先是作为一般的西方理论引介进来,后经瞿秋白、鲁迅等人的努力,开始被中国文艺界所接受,并在后来的解放区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在第二阶段中,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总结了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基本历史经验,解决了长期以来没有解决好的文艺的革命方向问题,不仅对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也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内容,并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指导党的文艺政策的基本方针。在第三阶段中,文艺不再成为政治的附属物,文艺理论研究也从单纯的政治研究中解放出来,对文艺自身规律的研究受到理论界的重视。虽然,从现实来看,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研究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它的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成熟了。
透过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的发生发展情况,我们应该得到如下一些启示:第一,对国外相关研究的介绍引入很重要,尤其是今天,我们要始终关注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状况,没有国际视野或全球意识,没有与国际学术的交流与对话,在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是没有出路的。第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居于主导地位的国家意识形态理论,因此,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必须处理好与当下政治的关系,保持文艺与政治必要的张力。第三,理论家需要走入现实而不是脱离现实,毛泽东《讲话》给我们树立了这一方面的光辉典范。因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必须切实关注中国的现实问题,做纯粹的书宅式研究同样是没有出路的。第四,我们要多从马克思、恩格斯等早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中汲取营养,以较高的理论视角来关注当下的理论问题。因此,对于刚刚进入该研究领域的学人来说,就还有一个重读马恩经典理论的问题。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深入阅读与学习,任何研究都将是缺乏根底的。除此之外,理论家们还要培养具有生命质感的研究激情以及善于反思的理论眼光,只有这样,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才能够真正走出属于我们自己的、不偏离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艺基本思想的发展之路。
[1].《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76页。
[2].张允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出版和传播》,《历史教学》1963年第7期。
[3].刘庆福:《马克思恩格斯文艺论著在中国翻译出版情况简述》,《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
[4].张允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出版和传播》,《历史教学》1963年第7期。
[5].译文可见瞿秋白《海上述林》,鲁迅编,1936年出版。关于这两篇通信,陆侃如《致哈克奈斯女士书》1933年由法文再译(1933年6月10日上海出版的《读书杂志》第3卷第6期),易萌《易卜生论——给保尔·恩斯特》1935年再译(1935年11月1日上海出版的《文艺群众》第2期)。
[6].刘庆福:《马克思恩格斯文艺论著在中国翻译出版情况简述》,《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
[7].刘庆福:《马克思恩格斯文艺论著在中国翻译出版情况简述》,《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
[8].艾克恩主编:《延安文艺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259页。
[9].由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组织翻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于1956年出版,其他各卷陆陆续续则于1985年底才全部出齐。
[10].王道亁:《恩格斯论海涅》,《文汇报》1950年7月13日。
[11].王道亁:《恩格斯论歌德》,《文汇报》1950年7月15日。
[12].王道亁:《恩格斯论卡莱尔》,《文汇报》1950年8月8日、9日。
[13].1980年,经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考研室再次编选,将篇目由原来的20篇左右增加到50篇,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出版。
[14].《马克思恩格斯论浪漫主义》一书,195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共四册)一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开始出版,至1966年出齐。
[15].介绍进来的主要有斯大林给高尔基、比尔-别洛采尔科夫斯基、杰米扬·别德讷衣等几位作家的信,以及1950年由解放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等。
[16].另外,还有一些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得以出版,如:《马克思论艺术和社会理想》(里夫希茨著,吴元迈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问题》(乔·米·弗里德连杰尔著,郭值京、雪原、程代熙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列宁文艺思想论集》(董立武、张耳编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等。
[17].这基本是当时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如张凌就以《“西马”非马》为题撰写文章,比较有代表性地表达了这种意见,见《美与时代》1992年第6期。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19].杜书瀛:《国际共产党人的文艺美学发展史》,《粤海风》2009年第4期。
[20].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9页。
[21].中央总学委:《中央总学委关于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通知》,《解放日报》1943年10月22日。
[22].《智取威虎山》剧组:《努力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红旗》1969年第12期。
[23].“小峦”(写作组名):《坚定不移,破浪前进》,《人民戏剧》1976年第1期。
[24].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全文在国内主要有两个版本,一个是由何思敬译、宗白华校,1956年9月人民出版社出版,标题为《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个是由刘丕坤译,1979年6月人民出版社出版,标题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979年9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中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文,系根据刘丕坤译文校订而成。
[25].关于“体系论”的讨论缘起是1980年刘梦溪在《文学评论》第1期上发表的《关于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几点意见》一文,该文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只有一些关于文艺论述的“断简残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以及毛泽东同志,并没有建立起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完整的理论体系”,由此拉开了这场讨论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