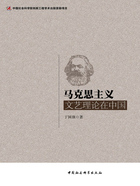
一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译介
以现有资料来看,在我国马克思的名字最早见于梁启超的文章中。1902年,他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中曾提道:“麦喀士,日耳曼国社会主义之泰斗也。”麦喀士即是马克思最初的中译名。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最早译文是1906年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第二号发表的《共产党宣言》的几个片段和十项纲领。[2]此后,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著作,主要是有关“社会主义”的文章,时有中文翻译。但由于当时译者不能真正理解马恩的思想,加上他们各取所需,因而译文质量参差不齐,并没有很好地传达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应有之意。1917年,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这种状况才得以改观。国内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并通过各种渠道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点(美学)也就在这一时期开始被介绍进来。
1919年,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该文从日文转译了马克思《〈经济学批评〉序文》(今译《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唯物史观的“概述”部分,其中关于艺术作为意识形态部门之一的观点,大概就是现今已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观点在中国的最早介绍。[3]1920年4月,上海出版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未译序言),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以完整的形式出版的第一个中文译本。[4]列宁文艺论著的最早中文译文是发表于1925年2月13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的《托尔斯泰和当代工人运动》(今译《列·尼·托尔斯泰和现代工人运动》);而列宁著名的《论党的出版物和文学》(今译《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的节译文1926年12月6日已发表在《中国青年》第144期上。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7—1937),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第一次开始比较大规模地被译介进来,主要有两条途径。第一条途径,主要是创造社、太阳社成员和鲁迅、冯雪峰等人从日文转译或翻译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著作,主要有马恩关于文艺的通信、列宁论托尔斯泰,以及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等俄苏文艺理论家以及日本学者有关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著作。例如,鲁迅翻译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文艺与批评》等;冯雪峰翻译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与社会生活》、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之社会的基础》、沃罗夫斯基的《作家论》、弗里契的《艺术社会学底任务及问题》、梅林的《文学评论》、日本升曙梦的《新俄罗斯的无产阶级文学》等;1934年胡风从日译本翻译了《与敏娜·考茨基论倾向文学》(《译文》第1卷第1期,今译《恩格斯致敏·考茨基》)等。1936年5月,郭沫若摘取马恩《神圣家族》中第五章和第八章有关文艺的重要段落,直接从德文原本翻译出版了《艺术作品之真实性》(1947年上海群益出版社重印时改为《艺术的真实》)等。
第二条途径,主要是从俄文翻译了一些普列汉诺夫、列宁等人的著作。在这方面,比较重要的代表人物,有曾担任过中国共产党主要负责人的瞿秋白,以及周扬等。如1932年,瞿秋白编译的《现实——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翻译了恩格斯、普列汉诺夫、拉法格的部分文艺论著,其中有当时新发现的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和致保·恩斯特的两封信[5]。同时,他还编译了《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恩格斯和文学上的机械论》两篇文章。1934年9月在《文学新地》创刊号上,他翻译发表了列宁的《列甫·托尔斯泰像一面俄国革命的镜子》。另外还译介了《社会主义的早期“同路人”——女作家哈克纳斯》的一些生活和创作的材料,以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马恩的文艺理论观点。1935年,易卓翻译了《恩格斯致拉萨尔》和《马克思致拉萨尔》(1935年11月1日上海出版的《文艺群众》第2期)。[6]至此,到30年代,马恩关于文艺问题的五封著名书信在中国已有了多种公开发表的节译或全译文。除以上翻译外,作为研究成果,1933年4月,周扬在《现代》杂志上发表了《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一文,第一次较为系统地向中国文艺界介绍并阐释了苏联文学界正在讨论、提倡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创作理论。
从1937年到1945年,中国经历了一场与日本的战争。战时的中国,形成了两个文化中心。一是国民党的临时首都重庆,二是共产党所在地延安。1939年11月,当时在国统区由欧阳凡编译的《马恩科学的文学论》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在桂林出版。1940年10月,由苏联马恩列学院文艺研究所编、楼适夷从日文转译的、从马恩著作中摘录辑集而成的《科学的艺术论》一书也由上海读书出版社出版。该书的出版,“第一次为中国读者提供了较为系统的马恩的文艺论述,标志着马恩的文艺论著在我国的翻译出版取得了重大进展”[7]。
延安解放区在翻译或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方面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当时比较成熟的编译本就有三种。第一本是1940年5月由新华书店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艺术》,该书由曹葆华、天蓝合译,具体由延安鲁艺翻译处组织,内容主要是马恩关于艺术的书信和列宁论托尔斯泰的论文等。“它是延安出版的第一本马列文论译著,具有开创和奠基意义。”[8]第二本是1943年4月由读者出版社出版的《列宁论文化与艺术》,由萧三翻译,内容涉及列宁论文化与文化遗产、列宁论艺术的阶级性及党性,以及几篇回忆“列宁与艺术”的文章等。第三本是1944年3月由解放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由周扬编选,内容主要选录了以上两本译著中的文字,除马恩列之外,此书还收入了斯大林、普列汉诺夫、高尔基、鲁迅、毛泽东有关文艺的评论和意见。该书后来一再重印,成为人们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艺思想的重要文献。除此之外,延安时期,《解放日报》还发表了一些马列文论的单篇译文,主要有列宁的《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恩格斯论现实主义》《列宁论文学》等。以上这些著作的编译出版,成为中国文艺工作者从事文艺实践与研究的重要理论资源。
新中国成立以后直至“文化大革命”前这一段时间,随着译介条件的大为改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文艺著作继续被大量地引介到国内。这其中除了1953年2月国家专门成立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开始有计划、有系统地翻译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外,[9]一些学者也在有选择性地翻译介绍马恩等经典文艺理论家的文艺理论著作。如在1950年7月、8月间,《文汇报》连续发表了王道亁翻译的《恩格斯论海涅》[10]《恩格斯论歌德》[11]《恩格斯论卡莱尔》[12]等文章。1951年,上海平明出版社还出版了由法国学者弗莱维勒(J.Freville)编辑、王道乾翻译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一书,该书更加系统地介绍了马恩的文艺思想。1951年,由曹葆华等同志翻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一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出版后曾多次修订重版,影响很大。[13]20世纪50年代,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也开始被翻译进来。195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贺麟以《黑格尔辩证法和哲学一般的批判》为名的节译本,1956年又出版了由何思敬译、宗白华校,以《经济学—哲学手稿》为名的全译本。除此之外,苏联当代美学家里夫希茨主编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浪漫主义》《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等,也都在这一时期翻译出版。[14]在里夫希茨《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一书中也有《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部分内容。除此之外,马恩关于民歌的一些论述和他们搜集的民歌作品,还有斯大林关于民间文艺的论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文学艺术的“竞赛”原则、语言的非阶级性问题[15]等,也在这一时期被介绍进来,这对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艺论著被大量地翻译进来,给这一阶段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带来了良好的机遇。研究者或根据现有的中文译本或根据手头的俄文版本,比较全面地展开了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学术研究。涉及的理论问题包括文学艺术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的不平衡关系、戏剧冲突、文学的党性原则,关于民间文艺、作家评论等。“文化大革命”期间,大部分知识分子在政治运动中受到牵连,被打成“右派”或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因此,这一时期,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成果不多,译介有限。
新时期以后,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整理与研究又恢复了以往的盛况。除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理论的整理与研究方面,出现了诸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等[16]著作外,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大量译入,成为这一阶段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美学)的重要收获。从20世纪80年代初一直到90年代末,可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们的著作几乎在国内都出现了译本或介绍性的读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由徐崇温主编、重庆出版社出版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分四批出版了西方学者的著作或国内学者的研究性著作达42部,出版周期几乎横跨整个90年代,同时也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与介绍推向了高潮。这套丛书成为国内学者认识与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资源,深深影响着90年代以后国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其他一些重要的研究专著,如冯宪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重庆出版社1997年版)、谭好哲的《文艺与意识形态》(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朱立元主编的《法兰克福学派美学思想论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马驰的《“新马克思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陆俊的《理想的界限——“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乌托邦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杨小滨的《否定的美学——法兰克福学派的文艺理论和文化批评》(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等,这些著作都从不同角度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美学思想进行了研究。90年代初,学者们对于“西马”的态度主要是排斥和批判,认为其为“非马”[17],但经过大量的介绍与研究之后,国内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已经从最初简单的唯物、唯心二元批判转变到真正的学术研究,对于“西马”的评价也发生了改变,承认了其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中的合法地位。今天,像梅林、卢森堡、拉法格、费希尔、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卢卡奇、葛兰西、柏拉威尔、马歇雷、佩里·安德森、勒斐伏尔、考德威尔、古德曼、阿尔都塞、本雅明、阿多诺、马尔库塞、威廉斯、詹姆逊、伊格尔顿、齐泽克等这些“西马”学人已经成为中国学者和文学研究者非常熟悉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