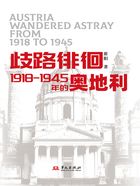
四、脱离德意志后的半个世纪
如果说1805年奥斯特里茨之战后奥地利没有被肢解是拿破仑出于维持欧洲均势的需要,那么1866年普奥战争后奥地利得以保留也是俾斯麦基于同样考虑的结果。
老谋深算的俾斯麦虽有“铁血宰相”之称,但并不是无限推崇暴力的军国主义分子。萨多瓦战役结束后,普鲁士朝野一片欢腾,上至国王威廉一世,下至普通士兵都想一鼓作气攻占维也纳。唯独俾斯麦能保持头脑冷静,极力反对彻底粉碎或合并奥地利。一方面是因为俾斯麦担心普鲁士过分的胜利会引起法俄等国干涉,不如见好就收,免得前期战果化为乌有;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俾斯麦对奥地利与普鲁士能在同一个屋檐下和谐相处不抱幻想。他后来在回忆1815年以来两国在德意志邦联内部纷争不休的历史时说:“如果它(奥地利)相应地改变自己的政策,与普鲁士协调一致,而不是通过多数派和其他势力来压制普鲁士,那么在德国我们本来是很可能经历或试行一段时期二元政治的。”然而,“这种二元政治是否能够以一种德意志民族感情可以接受的精神,持久地防止内部的分裂,和平地发展下去,这是值得怀疑的。”德奥两国一个多世纪的激烈对抗和彼此严重的不信任感,以及奥地利不肯轻易放弃自己在德意志传统领导地位的事实,都使俾斯麦认定普奥两国“在平等的基础上的一种生存方式成为不可能”。
纷繁复杂的民族问题,是促使俾斯麦放弃奥地利的另一重要原因。奥地利没有主体民族,政治上居于统治地位的德意志民族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还不到四分之一。马扎尔(匈牙利)、捷克、波兰等几个主要民族不仅占据了奥地利近60%的人口,而且普遍具有较强的离心倾向。19世纪以来,奥地利境内多次爆发民族革命,俾斯麦讽刺奥地利是“一条颠簸的国家航船”。此时合并奥地利无异于引火烧身,将会把尖锐的民族矛盾带入新成立的德意志帝国。那么只占领奥地利的德意志部分是否可取呢?俾斯麦说得很明白,那就会使奥地利的剩余地区,也就是“从蒂罗尔到布科维纳的欧洲这一广大地区”陷入分裂和混乱,导致德意志帝国失去东南欧的重要屏障。因此,俾斯麦得出了最终结论:“德意志—奥地利,无论作为整体还是部分,我们都不需要。”
由于俾斯麦的坚持,奥地利侥幸躲过了亡国的厄运。就1866年夏天的形势看,并不是没有这种可能的。当时连皇帝和皇后都准备逃往匈牙利了,结果却是奥地利除了丢掉威尼斯之外,领土基本保持完好,同时只需要向普鲁士象征性地支付一小笔战争赔款即可。但这并不是因为奥地利强大,而恰恰是因为它相对虚弱。
战败使哈布斯堡家族的权威暴跌,动摇了它的统治基础。为了延续国祚,1867年2月,皇帝被迫向匈牙利族让渡部分权力,将奥地利帝国重组为奥匈二元帝国。匈牙利升格为自主权更大的王国,由皇帝兼任国王,帝国的其余领土则被泛称为“西斯莱塔尼亚”。哈布斯堡家族做出妥协是为了向普鲁士复仇,期待有一天能够重新君临德意志,但德意志帝国的成立使哈布斯堡家族的这个愿望落了空。奥匈帝国和德意志帝国之上再也没有类似神圣罗马帝国或德意志邦联那样的超国家组织,德意志民族共存于德奥两国成为既定事实。
奥地利并不是唯一一个在1871年之后脱离了德意志的邦国,但它毕竟不同于卢森堡、列支敦士登那样微不足道的小邦。从民族统一的角度看,“小德意志”方案显然不够彻底。从名义上的德意志老大沦落到被逐出德意志形成的强烈反差,令许多推崇“大德意志”方案的奥地利人士大失所望。就在奥匈帝国成立当年,维也纳即出现了第一个德意志民族运动组织。它以萌发于拿破仑战争时期的泛德意志思想为指导,强调“所有说德语的德意志人都应生活在同一个国家”。很快,泛德意志思想在奥匈帝国传播开来,催生出了一大批形形色色的极端德意志民族主义者。
德意志民族派的首领格奥尔格·冯·舍纳雷尔就是此类人物的代表。他生于1842年,在维也纳的一个富裕家庭中长大,1866年以前一直在乡下打理自己的庄园。奥地利在普奥战争中的失败和德意志帝国的成立大大刺激了舍纳雷尔,从此他怀着对俾斯麦的仰慕弃农从政。舍纳雷尔主张摧毁奥匈帝国,将其德意志部分合并到德意志帝国。他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反对天主教、反对犹太人、反对占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总之奥匈帝国的一切他都反对。用舍纳雷尔自己的话说,就是“现在这个奥地利国家的一切都是腐烂的”。
1873年,舍纳雷尔当选帝国议员,没过多久他就以充满挑衅性的演讲出了名。大多数议员认为舍纳雷尔是一个政治争端的制造者,都非常讨厌他。在一次帝国议会上,由于赤裸裸地宣扬德奥合并,舍纳雷尔遭到了议员们的群起围攻,只得狼狈离场。
1882年,舍纳雷尔及其追随者在林茨建立“德意志全国同盟”并发布《林茨纲领》。纲领中极力突出“大德意志”理念,呼吁与德意志帝国密切合作、强化德语在奥匈帝国的使用。他号召奥匈帝国的德意志族以佩戴德皇威廉一世最喜爱的蓝色矢车菊和身披象征德意志民族主义的黑红金三色斗篷来表达对德意志人的身份认同,还鼓动受蛊惑的德意志族大学生到街头闹事,借此壮大组织的声势。
舍纳雷尔对组织成员有严格要求:必须是德意志族,不能有犹太或斯拉夫籍的亲戚或朋友,身体健康且只能与雅利安人通婚。舍纳雷尔以出色的演说技巧和鲜明的个性折服了大批信徒,被这些人尊称为“元首”。这个称号和他的许多理念后来都被另一个来自奥地利的狂人沿用。
处于内忧外患中的奥匈帝国无力阻止泛德意志思想的传播。帝国独特的二元体制依然保留了旧的王朝国家模式,它的弊端在于无法培养出超越民族认同的国家认同,帝国只能靠各民族对哈布斯堡王朝和皇帝的忠诚来维系才不至于分裂。“奥地利人”没有成为奥匈帝国全体人民的统称,而是退化为“帝国德意志族”的专指。
到19世纪七八十年代,维也纳、因斯布鲁克和格拉茨等地的高校成为激进德意志民族主义的重要阵地,宣传泛德意志思想的“德意志学生协会”吸引了大批德意志族学生加入。这些学生(也包括一些教师)以传唱德意志帝国国歌《德意志高于一切》为俾斯麦遥祝寿辰、反对天主教和犹太族裔等方式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更不用说许多普通德意志族民众仍对当年奥地利倡导的“大德意志国家”抱有深厚感情。
俾斯麦本人对此也深有体会。1879年,他出访奥匈帝国时写道:“在离开加施泰因经过萨尔茨堡和林茨的旅途中,各个车站上群众对我欢迎的态度使我深刻意识到,我是在真正德意志的土地上,是在德意志居民中间。”他由衷地感慨,即使德奥两国过去经历了一连串战争,但“奥地利德意志人的日耳曼感情……并没有被窒息”,两国仍是“血亲”。俾斯麦不想给奥地利留下长久的痛苦记忆。早在1871年秋天,在俾斯麦的建议和德奥统治阶层的共同意愿下,两国消弭了普奥战争以来的对立情绪,恢复了“德意志兄弟”的密切关系。
但俾斯麦能做的也就到此为止了。由于始终将奥匈帝国的存在当作德意志帝国必不可少的安全保障之一,俾斯麦对舍纳雷尔等人请援的呼声反应甚是冷淡。德意志帝国中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对帝国政策的影响也相当有限。俾斯麦去职后,年轻的皇帝威廉二世醉心于掠取海外殖民地,既无暇也无兴趣考虑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的合并问题。1897年,德意志帝国外交大臣伯恩哈德·冯·比洛在一份备忘录中直截了当地指出:“我国对奥地利德意志族为了增强内部凝聚力、保持德意志属性和维持奥地利现状所进行的斗争表示深切同情,但如果这种斗争是以寻求将奥地利的德意志地区分离出来和恢复1866年的状态为目的,那么这些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将得不到我国任何支持。”
在奥匈帝国国内,舍纳雷尔一派既无力独自推翻哈布斯堡王朝,又没有获得社会各阶层的一致认可,更缺乏外部势力的支持。德意志民族派至19世纪末就逐渐式微了。舍纳雷尔唯一的安慰,是死后得以安葬在距自己偶像俾斯麦墓地不远的一处地方。
奥匈帝国和德意志帝国共存了半个世纪。德奥合并作为一种政治理念,尚不具备可行性。两国合并的真正契机,还要等到20世纪初才能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