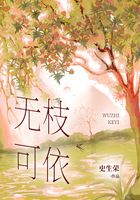
第3章 冲动后的冷静
新来的教师要试讲几周课。试讲期间,所在学科的领导和老教师都要轮番去听课,然后讨论指导。据说这是学校的光荣传统。让高怡不能接受的是把她也算在新教师行列,和那些二十出头的硕士甚至是本科生划成一类。她觉得这不仅让她想不通,道理和逻辑上也都说不过去。她是学校花大价钱引进的人才,既然是人才,就不是学徒,甚至也不是普通的教师。再说,读硕士前,她就在中学任教几年,而且本科读的就是师范大学,实习期间老师就指导过了。高怡觉得这事真的又有点荒唐,仿佛一下来到了荒唐国。副院长蔡红负责教学工作,高怡决定找找蔡红。
蔡红大概有五十岁左右,虽然是副院长,但在院领导中,算年纪最大的。高怡一肚子气,虽然竭力克制,也想好了只讲清理由,但口气还是有点冲,话也说得像连珠炮。好在蔡红不温不火,一言不发耐心听她的诉说,直到她说完,蔡红才平静地说,这个活动是学院安排的,不管怎么样,毕竟你是新来的,是第一次给大学生讲课。另一方面,你是学院引进的人才,而且三十万引进争论也不小,大家对你的期待也很高,也都想听听你这人才的课,一是看看你的真实水平,二来也是向你学习点什么。我觉得这本是一件好事,我不知为什么,你却认为不公平,甚至是对你的嫉妒。
听蔡红的口气,还是嫉妒,还是想看看她到底有多大的本事,但理由却是冠冕堂皇,这更说明了她的虚伪,也更证实了就是嫉妒心在作祟。文人相轻,现在不仅仅是相轻,简直就是报复戏弄。那天办公室的同事告诉她,说把办公桌搬进厕所的事,全校都知道了,而且全校一片骂声。骂学校糟蹋钱昏了头,骂学校搞形式赶时髦,也骂人才盲目牛皮又无才无德。又说不少教师说我们教了半辈子书,教学经验丰富并且学生反映也好,学校从来都没奖励过一分钱。花三十万引进一个没教过一天书的学生,倒要看看她能教出个什么水平。
她当时虽然愤怒,但她清楚,嫉妒她的,就包括这位同事。她当时觉得好笑,甚至还有点得意,觉得他们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去,反正钱已经到手,他们说他们的,我做我的。现在看来远不是那么回事,人们的嫉妒已经变成了嫉恨,已经变成了幸灾乐祸要看一场好戏。高怡痛苦了说,问题的根本不是你说的那样,如果是考察我的真实水平,如果是向我学习,就应该安排观摩教学,而你们通知的,却是试讲,然后再听你们指导。既然是向我学习,又怎么能是试讲。
蔡红笑了,高怡感觉蔡红的笑就是对她的嘲弄,就是猫抓住老鼠后的得意和玩弄。蔡红很快收起了笑,说,我刚才已经说清楚了,不管怎么说,你都是新来的,三十万并不能改变新来的这一事实,也不能因为三十万就搞特殊化。
这样说分明是故意整人了。你蔡红算什么东西,论文凭你最初只是大专毕业,而且最初是在财务室当会计,后来才调到学院。高怡气得浑身都有点抖,平静半天,还是脸红脖子粗地说,我也早已经说清楚了,大学毕业后,我就教过几年学,也可以算老教师了。
蔡红终于生气了,她阴了脸说,但你没教过大学生,我已经给你讲清楚了,再说这事是学院定的,我也没办法,你理解也得执行,不理解也得执行。
说完蔡红便转身在计算机前工作,高怡虽然还想争辩,但也只能出门。
高怡悲伤得想哭,但更多的是愤怒,她想立即去找院长,走几步,又觉得自己是不是又有点太冲动。遇事冷静思考,才是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智慧。回到办公室,她想给何子峰打个电话,听听何子峰的意见。何子峰不仅沉稳机智,性格品德也让她佩服。拿出手机,却发现手机又没电了。
手机的电池确实是不行了,算算,这个手机已经伴随了她五年,这五年虽然不常用,但手机表面的漆都快磨完了。手机破,功能也简单,样子也粗笨。还得买一个新手机。到处都需要花钱,这三十万也经不起几个折腾。
独自想一阵,高怡觉得还是应该找院长谈谈,这回不讲自己的理由,也不理直气壮,更不和人家争辩,只谈谈她的想法,也听听院领导对她的看法,看他们怎么说,怎么看。
院长也在计算机前忙,见她来,还算热情。这让她一下轻松了一点。情绪的变化,让她的叙述客观了许多,也带了许多的谦虚和自我批评。院长一直静静地听着,待她说完,然后才说,不管别人说什么,我觉得首要的是我们能干什么,要干什么。学校花三十万引进你,自然是要你在学科发展建设方面做出点事情。比如在学术方面,你应该利用你的学历和导师在社会上的学术关系,为学院申请到科研经费和硕士学位授权点,然后带领大家搞出一些研究,写出一些高质量的论文,然后获得一些奖励,最终提高学院甚至学校的知名度。同时在教学上,你也可以给学生树立信心,让学生知道,我们的师资队伍是过硬的,不仅有实践经验丰富的老教授,也有学历很高又是重点大学毕业的大博士。我想这些可能是你要考虑的。而那些人们的议论,生活方面的小事,我觉得你不应该过分地计较,计较了,反而显得没水平了。
高怡的脸一下红到了耳根。院长最后一句话让她无地自容。但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这些自己怎么就没有想过呢。她想作几句自我批评,但一时又不知怎么说才合适。好在院长转了话题,问她在科研方面有什么打算,能不能利用导师的影响和关系,弄来一些科研课题。院长说,这两年学校把科研列为院系考核的硬指标,而且指标是具体的,就是科研成果按科研经费来算,有多少万科研经费算多少分。咱们院是新学院,和人家老院系比,师资力量弱,科研经费就更少。考核指标上不去,咱们全院的津贴费就上不去。拿不到钱,大家都有怨言,所以我们当领导的压力就特别大。学校之所以花代价引进你,就是我一次次找校领导,一次次软磨硬泡跑来的。
原来是这样。高怡吃惊的同时,也感到使命重大,担子不轻。她的导师确实有名,是省经济学科的首席专家,也是学科评议组的组长,学科的科研项目和硕士授权点,也由导师任组长的学科组来评议。但导师却是一个只知埋头做学问的人,而且从不拉扯社会关系。要徇私为学院办点事,恐怕也难。刚才院长已经说得很明确,引进她,就是因为她的导师,就是为了科研课题和硕士授权点。但高怡不能实话实说,实说了,她就没有价值了。高怡只好说,我和导师的关系还不错,我们俩合著了一本书,初稿的很大部分是我写的,书正准备出版,很快就能印出来。至于申请研究经费的事,我考虑一下马上申请,争取申请成功。
院长鼓励一翻后说,咱们每年都要申报一些研究课题,但很少能获得成功。不成功的主要原因,就是学科组的专家成员里没我们的人。以后你要多和你的导师联系,争取在今年的研究课题评议时给帮帮忙。有了研究课题和经费,整个学院的科研教学就都活了,那个时候,大家也再不会有什么话说。
从院长办公室出来,高怡心里轻松了许多。但也感到自己真的是不成熟。来到学校不先和领导沟通,却先去计较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真的是有点幼稚。她在心里再把自己骂一遍,决定今天就去一趟导师家里,汇报一下近来的情况,然后再商量一下出书的事。
对自己执笔写的这本书,她是很有信心的。书是按教材体例编写的,内容除了导师的一些讲义,也融合了她全部的智慧和学问。导师和她都认为这本书写得不错,观点新颖,内容充实,而且从人性的本质特征出发来研究经济制度,是以前任何著述都没有过的。比如中国人,注重血缘,注重亲情,讲哥们儿义气,财富要留给子孙,过日子注重节约,不存点钱心里就不踏实等等。有这样的人性特征,就应该以此为前提建立合乎这些特点和本能的经济制度。记得书完稿后,导师特别选了一家有名的出版社,然后用特快专递把书稿寄了过去。但得到的回答是必须自己掏钱出书,自己负责销售。后来又寄了几家出版社,得到的结果却是同样的。导师非常气愤,当然也非常沮丧。现在看来,书有学术价值,自费出版又有什么可怕,如果学术界认可,出书的费用当然可以赚回来。她决定和导师商量一下,如果导师同意出点钱,就俩人合伙自费出版这本书。如果导师不同意,就她来掏钱出版。
花几万块钱出书,想想都有点心疼。但反复权衡,觉得出点钱出书也是必要的。一个学者要想确立自己的学术地位,唯一的办法就是著书立说,除此而外,没有它法。此时此刻,她更想有一本著作来证明自己的学问。她清楚,博士文凭只是一个学历证明,博士的水平也有高有低,S大有博士学位的教师也有二十几个,但如果有一本沉甸甸的著作加在博士学位上面,那就是金光闪闪的硬通货,哪个也得高看一眼,更不会有人说三道四。这样看来,花几万块也值得,如果书能得到认可,不仅可以把出书的钱收回来,说不定还能一举成名,然后名利双收。
毕业后还再没去过导师家,也应该去看看导师了,特别是得了三十万,怎么也得去感谢一下导师。导师生活简朴,也简单,补品和奢侈一类的东西他都反感,反复考虑,高怡到商场给导师买了一件羊绒围巾。导师年纪大了,天冷了出门需要一条围巾。
晚上来到导师家,导师的心情很是愉快,但导师并没多问那三十万,只是鼓励她多看点书。谈到那本书稿,导师的脸色暗淡了下来,但他仍不同意掏钱出版。高怡想说她掏钱出,突然觉得这样会更伤导师的自尊,便改口说省科学出版社有出版的意向,她明天去和人家细谈。导师立即又恢复了平静,然后说,这件事你看着去办吧,给不给报酬都没关系,不是自己掏钱出书就行。自己掏钱出书,那就是自己欺骗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