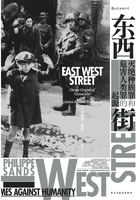
27
1910年,劳特派特与他的父母和哥哥妹妹一起离开了若乌凯夫。5在弗朗茨·约瑟夫一世自由主义统治下的第62年,时年13岁的他到伦贝格去接受更好的教育。同年,一匹名叫伦贝格的马获得艾普森德比赛马大会的冠军,马主人是英国的单身人士阿尔菲·考克斯,与这座城市并无明显的联系。6
阿龙在市郊管理锯木厂,他的儿子进入人本主义文理学校,已经成为一个出众且口齿伶俐的少年了。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书籍,自信,关心政治,不愿遵循宗教的道路。他的同龄人把他视为领袖,一个有文化的、意志坚强的、疾恶如仇的、有着“非常好的头脑”和良知的少年。建立在仇外心理、种族主义、群体认同和冲突的基础之上的社会不公在伦贝格的街道上蔓延,这些因素从小就触动了他。
劳特派特在若乌凯夫已经了解了群体之间的摩擦,因为宗教信仰和政治理念而产生的分歧被深深刻进日常生活中。他和莱昂一样了解到, 伦贝格提供了一种更加血腥的诠释,这座城市建立在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野心的断层带上。然而,即使是挤在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文明夹缝之间的正统犹太人家庭,劳特派特一家也相信自己生活在大都会里,作为自由文明的中心,这片天空下具有创造才能的数学家和无畏的律师,有挤满了科学家的咖啡馆,有诗人和音乐家,城市里有崭新的火车站和宏伟的歌剧院,这也许会是“水牛比尔”科迪想要造访的地方(1905年,他确实带着他的“狂野西部秀”来过了)。7

这也是一个有着自己的声音和气味的城市。约瑟夫·维特林写道:“我可以听到利沃夫的钟声响起,每一次响声都不一样。我可以听到市集广场上喷泉的飞溅声,被春雨洗去尘土后,散发着芳香的树木飒飒作响的声音。”年轻的劳特派特很可能像维特林一样经常光顾这些现在已找不到踪迹的咖啡馆:在亚格隆尼路和五月三日大街拐角处的那家“欧洲人”(在那里,“女性成员的出现是件令人不安的稀罕事”8),在安德里奥利通道的上层的那家“艺术”(在那里,“每当长发的小提琴手瓦瑟曼开始演奏舒曼的《梦幻曲》时,富有情调的灯光就会立刻配合地调暗”),以及五月三日大街和科修斯柯街交叉路口的那家“文艺复兴”(来自其他咖啡馆的服务员会穿着耀眼的上衣打着彩色的领带光顾这里,吆喝同行出来招待他们)。
在这家人来到伦贝格三年之后,战争也来到了伦贝格。俄国人在1914年9月占领这座城市的时候,劳特派特当时正身处其中。沙皇尼古拉二世接到消息称,奥地利已完全被击败,撤退时“溃不成军”9。莱昂的哥哥埃米尔很可能就是在这场大战役中战死的。《纽约时报》报道,俄罗斯“入侵者”表现出了“仁慈”,尊重了教堂和“路边的祈祷中心”,这使伦贝格得以保持平静和繁忙,而伦敦在战争中却陷入了血腥骚乱。10
1915年6月,奥匈帝国军队在德国军队的帮助下重建了这座城市,“在整个奥地利和德国迸发了狂喜”11。一个月之后,劳特派特被征入了奥地利军队,然而他似乎大部分时间都借住在他父亲的锯木厂里。一个朋友在发动机房看到他,“仿佛听不见”机器和战争的声音,沉浸在书本里,自学法语和英语。12劳特派特留下了一本记录详细的笔记本,现在由他的儿子保管着,他在里面写下了他读过的书籍,横跨众多领域,包括战争和经济学、宗教和心理学、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专著。音乐让他可以暂时逃避现实,特别是巴赫和贝多芬,在他的一生里都给他带来激情和安慰。据说他有“非凡的鉴赏力和音乐记忆”13,但他本人的演奏能力不超过用两根手指弹《克鲁采奏鸣曲》的程度。
时间到了他需要做出大学生活选择的时候,他的父母说服他跟随他哥哥的脚步。1915年秋,他进入伦贝格大学的法律系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