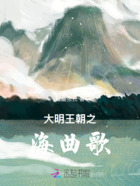
第3章 芾棠暗涌
【嘉靖三十三年七月】
【青州府·张宅】
张继棠的书房内,沉水香在鎏金狻猊炉中袅袅升起,窗外树影婆娑。
“芾霖,昭宁差点被安东卫的人带走,这事儿......”七叔公推门而入,话音未落,张继棠已抬手示意。
“七叔,你不来,我也正要寻你。”他声音低沉,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案上那方“海隆盐号”的铜印,“雷刚已向我禀过,那王承宪我也派人打听过了,”他顿了顿,目光微沉,“王承宪是王宪之子。”
七叔公瞳孔微微一缩:“王宪…?我想起来了,嘉靖二十三年抗倭的王指挥使?”
“正是。”张继棠起身,推开雕花槅扇,暮色斜照在墙上悬挂的《山东运河泉源图》上,这幅图标注了山东所有水系运输线路。
“当年,我们还在莒南老家。父亲早逝,家业刚起就风雨飘摇,全靠七叔您带着我苦苦支撑。”他喉结滚动,声音微哑,“岂料那倭寇又趁火打劫....若非王宪大人率水师出海截击,我们恐怕早已家破人亡。”
七叔公沉默良久,目光投向远方,缓缓道:“那年倭寇来犯,真是一场浩劫啊。他们放火烧了盐场,杀害官兵,劫掠粮钱,还掳走了镇上好几个妇孺。那些被掳走的人家,都道是再也见不着亲人了......”他顿了顿,眼中闪过一丝欣慰,“可谁曾想,后来竟都被救回来了!”
“但不久,王大人却遭到弹劾,调离了安东卫,我们这些年…与那王家也不曾有往来。”
他忽然转身,目光如炬:“可如今,他儿子王承宪刚任安东卫佥事,掌石臼所,就微服私访,稽查倭货——必是得了什么风声。”
七叔公眉头紧锁:“前几日,他与昭宁在东关街相遇是偶然,还是......”
“当是偶然!”张继棠猛地截断,沉默片刻。
“无论如何,”张继棠深吸一口气,转身看向七叔,“你着手给宁儿选几个女护卫吧,日后她总要打理海隆盐号的生意,一个女子出门,就跟着妙音那丫头,太不安全。”
“女护卫,这个主意好,我这就去办。”七叔公点头,却又迟疑道,“只是......宁儿才十四岁,性子纯善,又自幼锦衣玉食,对这商场无情、世道险恶还所知甚少,现在是否要将这些担子压在她的身上?”
“我明白,此事还是容我想一想。”张继棠闭了闭眼。“所以,许多事,还得劳七叔多费心。”
七叔公深深看他一眼,终是郑重颔首:“放心。”
待七叔公离去,张继棠独自站在窗前,忽然低声喃喃:“爹,儿子不孝......”
他抬手抚过案头账册,“儿子已经年逾四十了,膝下人丁单薄,昭宁虽然聪明、乖巧,但毕竟是儿女身。”
“这个经商之道,儿子也如履薄冰。当年您说'商道即人道',可何谓商道,何谓人道?儿子始终琢磨不透啊。”
窗外忽起风,吹得那《山东运河泉源图》哗啦作响,千头万绪,张继棠猛地合上册子,仿佛被烫了手。
【张府·冰壶轩】
冰壶轩内,赵干办正立在紫檀案几前给昭宁讲课,“这《盐政利弊考》,是盐商子弟的命脉。这门学问要讲什么,无非三件事——第一,利从何来;第二,祸如何避;第三人如何交。”
“就拿这第一,利从何来讲,这“盐引是明路,窝本是暗门。”
昭宁突然打断:“海隆盐行的账本上'窝价'写成'修缮费'。
赵干办一愣:“的确如此。贿赂盐运司官员,提前锁定未来几年的盐引配额,称为“窝本”,此乃常例也。
他继续道:“除此之外,这暗门还有虚报灾损。领引十张,实支二十,场官得三,运司得五,余者自取。此也乃常例也。”
“如若如此,盐场盐不够支取怎么办?”昭宁蹙眉
赵干办眯着眼:“超发部分?自然是让灶户日夜赶工补上。”
话音未落,张继棠负手而入。
“爹。”昭宁担心爹爹因为上次乞巧节惹来祸事,会训斥自己。但张继棠却和蔼的问道:宁儿对这‘利从何来’如何看啊?”
“这运司如虎,盐场如狼,不与肉食,反噬其主。我们要从中获利,就得喂饱他们。”昭宁顿了顿,“只是…这肉从何来?”
“是啊。“张继棠目光深邃,“昭宁可有答案?“
昭宁语塞。
“罢了,今日的课业就到此。爹今日要启程和赵干办一起去涛雒盐场——那里新出产了‘玉华盐’。”
“老爷,玉华盐,可是直供光禄寺的贡盐?”赵干办闻言激动。
“正是。”张继棠抚须。
“若我们也能拿到这贡盐的盐引,经光禄寺直供亲贵,虽说这产量不及普通盐,但利润可十倍于普通盐。”赵干办搓着手:“那我们到时候。。。”
“到时候,我们就不需通关节,广引额了!”
“涛雒盐场?”昭宁眼睛一亮“女儿想和爹爹同去!”
“不可!”张继棠断然拒绝;“自从你八岁那年跌落卤池,险些丧命,我就再也不许你去涛雒。”
“爹,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女儿现在大了,怎么会跌落卤池。”昭宁跺脚。
“好了,此事就这样定了。”张继棠不容置疑。“这些日子多陪陪你母亲,筹备五日后的府宴。等爹回来。”
“哦?是有什么喜事。”昭宁问到。
张继棠只补了句:“还有,你七叔公正在为你择选女仆护,出门跟着爹放心,回来便带你见见,让你亲自挑选。”
听到择选女护卫,昭宁顿时转嗔为喜。她想起了水浒里的故事。“难道这女护卫都像那顾大嫂、孙二娘、扈三娘那样?”
想到这里,她唤出妙音。“备轿,我们去醉仙楼。”
【青州府·醉仙楼】
醉仙楼二楼的听雪阁里,湘妃竹垂下,妙音静立在侧,昭宁坐着正在品茶。她突然一蹙眉:“这六安松萝真苦。”
帘外是说书先生醒木一拍,今日没讲到《水浒》女将,讲的倒是《水浒传》里“燕青智扑擎天柱”的段子——
“那燕小乙佯装不敌,待擎天柱扑来时,忽使个'鹞子翻身',反将那厮掼下擂台!”
台下喝彩声四起。
“宁妹妹也爱听《水浒》?”一道清朗声音传来。昭宁抬头,只见万振林一袭素白直裰掀开竹帘,含笑踏入:“方才见听雪阁来了人,便知是你。”他轻拂衣摆,在昭宁对面坐下,“这阁子平日都是姑父包下,今日难得见你在此。”
昭宁挑眉:“万公子不在明伦堂治学,倒有闲心听市井话本?”
万振林轻笑:“我听说表妹也日日在‘听雪阁’听讲,今日也得闲来听这市井话本?”说着在昭宁对面坐了下来。
昭宁微微一惊,这“听雪阁”是父亲专为自己设在耳房的听讲之处,万振林竟然知道确切的名字。
“万家哥哥可是在揶揄我?”
“哈哈,不曾不曾。”万振林摇头。
“这《水浒》故事快意恩仇,多有趣呀。”昭宁话里流露出羡慕:“特别这水浒女将,个个身手了得,来去自如。”
“不过,朝廷里现在有人抨击这话本‘倡乱诲盗’。”万振林稍稍顿了一下,“哈哈,不过我倒觉得这样的说法太过夸大其词。这水浒看似草莽,实在暗藏大义。就譬如这燕青吧——”
帘外说书人的声音陡然拔高:“那小乙哥褪了青衫,露出雪缎似的皮肉,那身花绣在日头下活像玉雕上爬满了春藤——“醒木啪地一响,“道君皇帝当场喝彩:'好个锦体浪子!'”
满堂哄笑声中,昭宁却将茶盏往案上重重一搁。她不喜欢这等粉面绣花的男子,倒爱粗粝些的,譬如......
“宁妹妹这神色,莫不是我方才说的有什么不妥之处?”万振林突然倾身,衣袖带翻了一碟松子。
昭宁猛地回神:“哦不......”她指尖无意识摩挲着腕间鎏金镯,“我是说,这‘倡乱诲盗‘的评价不过是文人牵强附会。那这燕青后来如何了?”
万振林敛了笑意,“罢了,不说这《水浒》了。”他从袖中滑出一封泥金帖子,轻轻推过案几:“五日后贵府设宴,姑父的七品’文林郎‘敕牒就要到了。”
“当真?”昭宁手一抖,茶盏险些脱手。“这文林郎是多大的官儿?可是飞玄真君亲封?”
“当真。”万振林点头,“衡王府长史亲自请封,由吏部合议的,七品官,想来我父亲也是七品,现在二人是同品级了。”
昭宁眸光微闪,“花了多少银子?”
“少说也有500两吧。”
昭宁脸上浮起笑意:“也值!父亲有了官身,往后办事儿也方便多了。母亲、七叔公、祖母定会欢喜。”
万振林凝视她片刻,轻声问:“宁妹妹真这样认为?”
“自然。”昭宁笑吟吟道,“身披冠带,光耀门楣,为何不欢喜?”
万振林沉默一瞬,忽而起身拱手:“海岱诗社几位友人在此,我先失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