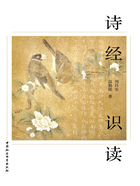
一 何人为《诗》:《诗经》的作者
《诗经》的作者问题,是《诗经》阅读和研究中最难判断的。《诗经》的作者究竟是什么人?历代学者都有探讨,论说纷纭,很难有统一的意见。不过,我们注意到,在汉代的《诗序》中,已经透露了一些信息,例如《关雎》,《诗序》说:“后妃之德也”;《葛覃》,《诗序》说:“后妃之本也”;《卷耳》,《诗序》说:“后妃之志也”;《七月》,《诗序》说:“陈王业也。周公遭变,故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鸱鹗》,《诗序》说:“周公救乱也”……在《诗序》看来,《诗经》的作者并不成问题,至少是可以寻得出大致身份的——其中以王公贵族大臣或后妃居多。《诗序》的这种推断或推断方式,遭到古往今来不少学者(特别是现代学者)的猛烈批评。如郭沫若对《诗序》关于《诗经》作者的看法批评最力,他在《十批判书·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里这样说:
《诗》三百篇的时代性尤其混沌。《诗》之汇集成书当在春秋末年或战国初年,而各篇的时代性除极小部分能确定者外,差不多都是渺茫的。自来说《诗》的人虽然对于各诗也每有年代规定,特别如像传世的《毛诗》说,但那些说法差不多全不可靠。例如《七月流火》一诗,《毛诗》认为“周公陈王业”,研究古诗的人大都相沿为说,我自己从前也是这样。但我现在知道它实在是春秋后半叶的作品了。就这样,一悬隔也就是上下五百年。[18]
郭沫若的这种批评代表了当代学者的一些看法。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深入分析《诗经》的具体内容,关于《诗经》的少数篇章,《诗序》的结论则并无臆断,而是言之有据,即如郭沫若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里所言,《诗经》作者“极小部分能确定”。综观前贤的研究,对《诗经》的作者,可以从四个层面来认识。
(一)《诗经》中言明的作者
在《诗经》原诗中标明作者的,一共有四位,他们是:
1.家父。《小雅·节南山》:“家父作诵,以究王讻。”
2.孟子。《小雅·巷伯》:“寺人孟子,作为此诗。”
3.吉甫。《大雅·崧高》:“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大雅·烝民》:“吉甫作诵,穆如清风。”
4.奚斯。《鲁颂·閟宫》:“新庙奕奕,奚斯所作,孔长且硕,万民是若。”
这五首诗是《诗经》中仅有的几首标明作者的诗。对这几位诗人的身份和生平,典籍记载不多。其中“家父”,郑玄《毛诗传笺》认为系周大夫之字,其在鲁、齐、韩三家诗中均写作“嘉父”。《汉书古今人表》著录其名,朱熹认为,其时当在周桓王之世。这里的孟子不是战国时代的儒家大思想家孟子,因为在他的前面冠有“寺人”一词,是古代宫中的阉人,《汉书古今人表》中也有其名。吉甫是《诗经》中唯一注明作有两首诗(《崧高》《烝民》)的人,为周宣王时代(前827—前782年)的尹,史称尹吉甫,即兮伯吉父。兮氏,名甲,字伯吉父(一作甫),尹是官名(辅弼大臣)。《诗经·小雅·六月》颂美他征猃狁的武功,今尚有其遗物《兮甲盘》(金文),《汉书古今人表》也有其名。但《诗序》却就此生发开来,将《大雅》中《韩奕》《江汉》的著作权也归于吉甫名下,并均以为是“美宣王”之作。由于《诗序》不能提出较为有力的证据,因此也难令后人信服。关于奚斯,理解有歧义,有人认为是说诗的作者是奚斯,有人认为是说奚斯建筑了新庙。奚斯是鲁僖公(前696—前627年)时鲁国大夫公子鱼。其事见载于《左传·闵公二年》《史记·鲁周公世家》等。
(二)先秦典籍载明的作者
先秦典籍也有多处记载《诗经》的作者,兹列如下:
1.许穆夫人作《载驰》。《左传·闵公二年》:“许穆夫人赋《载驰》。”按,《载驰》在《鄘风》里。
2.公子素作《清人》。《左传·闵公二年》:“郑人为之赋《清人》。”“郑人”指郑文公,娶江氏,生子公子素(或称公子士),《汉书古今人表》作公孙素。《左传·宣公三年》也有记载。按,《清人》在《郑风》里。
3.卫人作《硕人》。《左传·隐公三年》:“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也。”按,《硕人》在《卫风》里。
4.秦人作《黄鸟》。《左传·文公六年》:“秦伯任好(按,即秦穆公)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钅咸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史记·秦本纪》也有类似记载。按,《黄鸟》在《秦风》里。
5.秦哀公作《无衣》。《左传·定公四年》:“秦哀公为之赋《无衣》。”《史记·秦本纪》也有记载。按,《无衣》在《秦风》里。
6.周公作《鸱鸮》。《尚书·金縢》:“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于后,公乃为诗以贻王,名之曰《鸱鸮》。”按,《鸱鸮》在《豳风》里。
7.周公或召穆公作《常棣》。《国语·周语中》记周襄王十三年(鲁僖公二十年,即前640年),周大夫富辰谏阻襄王讨伐姬姓郑国,作此诗。《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则记召穆公(召伯虎)作此诗。按,《常棣》在《小雅》里。
8.卫武公作《抑》。《国语·楚语上》:“昔卫武公年数九十有五矣……于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懿》,韦昭注说:“《懿》,《诗·大雅·抑》之篇也。‘懿’,读之曰‘抑’。”按,《抑》在《大雅》里。
9.周公作《文王》。《吕氏春秋·古乐》:“周文王处岐……周公旦乃作诗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按,《文王》在《大雅》里。
10.周公作《时迈》。《国语·周语上》说,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谏曰:“不可。……是故周文公之《颂》曰:‘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左传·宣公十二年》则将《时迈》的著作权归于周武王名下,说:“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櫜弓矢。我求懿得,肆于时夏,允王保之。’”按,《时迈》在《周颂》里。
11.芮良夫作《桑柔》。《左传·文公元年》载秦穆公言曰:“周芮良夫之诗曰:‘大风有隧,贪人败类。听言则对,诵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贪故也,孤之谓也。”按,《桑柔》在《大雅》里。
(三)汉代《诗经》学派认定的作者
汉代四家传《诗》者,对三百篇的作者也提出了不少的说法,现存的《毛诗序》标明《诗经》作者的有33 篇,其中国风有11篇,雅诗有21 篇,颂诗有1 篇,如认为《邶风》中的《绿衣》《燕燕》《日月》皆是卫庄公所作,《鄘风·柏舟》是卫共姜所作,《小雅·何人斯》是苏共刺暴公而作,《大雅·抑》是卫武公讥刺周厉王而作,《大雅·民劳》是召穆公讽刺周厉王而作。三家诗早亡,但零星材料流传至今,其中也有一些对于诗篇作者的揭示解说文字,如韩诗认为,《邶风》之中的《燕燕》是卫国定姜所作,《柏舟》是卫宣姜自誓所作;齐诗云:“卫宣公之子寿闵其兄伋之且见害,作忧思之诗,《黍离》之诗是也。”这些说法在其各自学派内部传习沿用,是否有所依据,我们已经难以考明,其基本特色是道德化、历史化与政教化,今人对其说也多持怀疑的态度。至于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云:“《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语纯为自勉,并非切合诗篇创作实际而言,不能视为严格的论断。
夏传才先生说:
即使以上可信或比较可信的知道作者的诗篇,仍不到305篇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九十以上诗篇的作者仍无从查考。而且即使知道了作者之名,除了个别人,我们对他们的事迹,仍然知之甚少。例如,《巷伯》是寺人孟子所作,我们也知道他是一位内府供职的小官,这和知道“为下层士吏所作”是一样的;我们知道凡伯或曹公作某诗,这和知道是公卿所作,也没有区别。逐一考查三百篇的作者是办不到的事,我们只能根据诗篇的内容和时代背景,大体上了解作者的身份,争取能了解一些作诗的本事。[19]
这个判断基本上是符合历史和诗篇实际的。
(四)后世学者推论的作者
后世学者对诗篇作者的姓名和身份有不少的探讨,如北宋王安石在《字说》里曾根据《小雅·巷伯》“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句并结合许慎《说文解字》关于“诗”乃“言”与“寺”合成的象声字(形声字)之说提出:“诗为寺人之言。”南宋朱熹《诗集传》认为,《卫风·氓》是弃妇悔恨之辞,明代何楷《诗经世本古义》认为,《秦风·晨风》是秦穆公悔过之诗,清代崔述研读《邶风·燕燕》认为,“此诗之文,但有惜别之意,绝无感时伤遇之情,而诗称‘之子于归’者,皆指女子之嫁者言之”“恐系卫女嫁于南国,而其兄送之之诗”;牟庭《诗切》认为,《郑风·野有蔓草》乃卫夏姬所作。
“五四”以来,学者们运用多种方法研究《诗经》,在作者问题上也有许多见解,如认为《魏风·伐檀》是伐木造车工匠所作,《唐风·杕杜》的作者可能是个乞丐,虽然持之无故,但能言之成理,给人一定的启发。今人的说解,虽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推测臆断的成分较多,逻辑推理也不够严密。如叶舒宪在《诗经的文化阐释》一书中,根据前人的研究,提出寺人是《雅》《颂》的主要作者,尹人也是《颂》和《雅》的作者群,盲官是《诗经》的传诵与加工者;萧甫春在《〈国风〉原是祭社诗》一文中认为,瞽工是《风》的作者队伍。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学者李辰冬研究《诗经》数十年,著有《诗经研究》《诗经通释》《诗经研究方法论》诸书,他运用现代统计学方法去探寻尹吉甫率军东征西讨的历史足迹,“发现”《诗》三百都有史实依据可征。李辰冬更为重大的“发现”还在于:“三百篇的形式有点像民歌,实际上,作者是用民歌来表达他的内心,并不是真正的民歌,民歌无个性,而三百篇篇篇有个性。所谓个性,就是每篇都有固定的地点、固定的时间、固定的人物、固定的事件。”李辰冬因此而提出,《诗经》乃尹吉甫在从周宣王三年到周幽王七年(前825—前775年)50年间一人所作。[20] 此观点可谓惊世骇俗,不啻向《诗经》学界甩出一颗重磅炸弹。但由于其推测成分多于实证分析,只不过是哗众取宠、耸人视听而已,学界并没有人相信、认可其说。
因此,可以这样认为,《诗经》中的作品,有的是贵族士大夫所作,有的是朝廷乐官所作,有的出于民间,创作者来自广泛的社会阶层,作者的名姓除了诗句之中明言者外,其他难以实考,还有进一步探研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