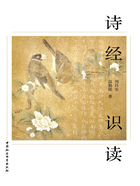
三 《诗经》的价值
作为中华文化的元典作品,《诗经》自问世以来,一直有着崇高的历史地位,它不仅是殷周时代的文学艺术,而且是上古诗歌艺术的集大成之作;它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而且是中国上古社会生活及文化精神的诗的凝聚和艺术的升华,有诸多方面的价值。
(一)社会政治价值
《诗经》中的许多诗,尤其是《雅》《颂》,当初就是政治家为政治目的而创作的,是被当作政治工具而加以运用的。《诗经》时代以“礼乐”治国。周人所说的“乐”就是诗、乐等文学艺术的统称。当时诗乐合一,诗为乐之词,乐为诗之声,单言诗、乐,常兼指二者。我国古代格外注重诗乐的政教功能,认为“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乐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人之道也,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于此也”[7]。诗乐是人们思想情感的真实自然流露,“唯乐不可以为伪”。人之情并非主观无端生发,而是感动于外在客观社会的:“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政治成败决定人心哀乐,人心哀乐决定诗乐之哀乐,“声音之道,与政通矣”,政治决定诗乐,诗乐反映政治,审乐以知政,“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追求“同民心而出于治道”[8],以诱发喜乐敬爱之心,以防哀怨之声作。
我国古人还认识到诗乐不仅反映政治,而且有助于政教,“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易,故先王著其教焉”[9]。“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10],赵岐注曰:“仁声,乐声,《雅》《颂》也。”仁声是寓教于乐,可以潜移默化地启发引导人自觉趋善,远比仁言的抽象说教更为有效。于是,周代统治者大规模地制礼作乐,将“乐”作为最重要的教化工具。
《诗经》的编集本身在春秋时代,其实主要是为了应用:作为学乐、诵诗的教本;作为燕飨、祭祀时的仪礼歌辞;在外交场合或言谈应对时作为称引的工具,以此表情达意。通过赋诗展开外交上的来往,在春秋时期十分广泛。《左传》中有关这方面情况的记载较多,有赋诗挖苦对方的(《襄公二十七年》),有因听不懂对方赋诗之意而遭耻笑的(《昭公二十年》),有因小国有难而请大国援助的(《文公十三年》),等等。这些地方引用的《诗》,或劝谏,或评论,或辨析,或抒慨,各有其作用,但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凡所称引之诗,均“断章取义”——取其一二而不顾及全篇之义。这样做的目的在于“赋诗言志”。赋诗言志的另一个功用表现,切合了《诗经》的文学功能,是真正的“诗言志”——反映与表现了对文学作用与社会意义的认识,是中国文学批评在早期阶段的雏形。如《小雅·节南山》:“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大雅·民劳》:“王欲玉女,是用大谏”,等等。诗歌作者是认识到了其作诗的目的与态度的,以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表达自己对社会、人生的态度,从而达到歌颂、赞美、劝谏、讽刺的目的,体现了《诗经》的文学功能及其文学批评作用。《诗经》还有它的政治价值,当时的社会(包括士大夫与朝廷统治者在内)利用它来宣扬和实行修身养性、治国经邦策略,这既是《诗经》编集的宗旨之一,也是《诗经》产生其时及其后一些士大夫所极力主张和宣扬的内容。孔子提倡的“诗教”,强调了《诗》自上而下的教化作用,其中尤其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强调了统治者应通过《诗》向百姓作潜移默化的伦理道德教育,使之成为一种社会风尚,从而有利于社会秩序的建立与统治的巩固。《毛诗序》有关《诗经》教化的理论,无疑大大强化了《诗经》的社会功用,也大大提高了《诗经》的地位,使之成了统治者实施统治的必备工具,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二)历史、民俗价值
首先,《诗经》的历史价值决定于它的真实性。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历史灾难,“现存先秦古籍,真赝杂糅,几乎无一书无问题”[11]。《诗经》篇幅短小,且又押韵入乐,便于记诵,因而被广泛应用,普及程度高,文字记载与口耳相传两条流传渠道使《诗经》得以真实、完整地流传下来。《汉书·艺文志》云:“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12] 汉代传《诗》有齐、鲁、韩、毛四家,他们对《诗》的诠释虽有出入,但就四家诗文本而言,仅仅是本字、借字之类非本质性的差异。《诗经》的真实性决定了其珍贵的史料价值,故梁启超赞曰:“其真金美玉、字字可信者,《诗经》其首也。”[13]
其次,《诗经》的历史价值体现在它创作时代之早上。《诗经》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集。诗之创作始自西周初期(前11 世纪)至春秋中叶(前6世纪)。若《商颂》确为商末作品,那么,《诗经》的创作年代还要前提一二百年。在世界文化史上,就时代而言,可与《诗经》及中国古代另两部典籍《尚书》《周易》相匹敌的恐怕只有古埃及的《亡灵书》(前26世纪零星的宗教咒语)、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前18世纪的法律条文)。古代以色列《圣经》最古老的部分是前9 世纪的作品,《荷马史诗》记述的虽是前12世纪的历史,而创作时代却是前8 世纪—前6 世纪,而且《荷马史诗》还更多地带有人类童年时期的宗教神学色彩,而《诗经》则更多地表现出只有理性觉醒时代才可能出现的尚实的价值取向。《诗经》不仅是中国文学、文化的源头,也是世界文学、文化的源头之一。
最后,《诗经》的历史价值体现在它内容的真实性、丰富性、广泛性上。《诗经》实际上全面反映了西周、春秋时期的历史,全方位、多侧面、多角度地记录了从西周到春秋(亦包括商代)的历史发展与现实状况,其涉及面之广,几乎包括了社会的全部方面——政治、经济、军事、民俗、文化、文学、艺术等。后世史学家在叙述这一历史阶段的状况时,相当部分依据了《诗经》的记载。如《大雅》中的《生民》等史诗,本是讴歌祖先的颂歌,属祭祖诗,记载了周民族自母系氏族社会后期到周灭商建国的历史,歌颂了后稷、公刘、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等的辉煌功绩。这些诗篇的历史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它们记录了周民族的产生、发展及灭商建周统一天下的历史过程,记载了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大迁徙、大战争等重要历史事件,反映了周民族的政治、经济、民俗、军事等多方面情况,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史料。虽然这些史料中掺杂着神话内容,但不可否认的是也包含着可以置信的史实。
《诗经》的民俗价值是显而易见的,体现在恋爱、婚姻、祭祀等多个方面。如《邶风·静女》写了贵族男女青年的相悦相爱;《邶风·终风》是男女打情骂俏的民谣;《郑风·出其东门》反映了男子对爱情的专一。这些都是从不同侧面和角度反映、表现各种婚姻情状的诗篇,综合地体现了西周春秋时期各地的民俗状况,是了解中国古代婚姻史的很好材料,从中也能了解到古代男女对待婚姻的不同态度和婚姻观。
《诗经》中不少描述祭祀场面或景象的诗篇,以及直接记述宗庙祭祀的颂歌,为后世留下了有关祭祀方面的民俗材料。如《邶风·简兮》中写到的“万舞”,以及跳“万舞”时伶人的动作、舞态,告诉人们这种类似巫舞而被用之于宗庙祭祀或朝廷的舞蹈的具体状况。更多更正规地记录祭祀内容的诗篇,主要集中于《颂》诗中。如《天作》记成王祭祀岐山,《昊天有成命》为郊祀天地时所歌。这些诗章充分表现了周人对先祖、先公、上帝、天地的恭敬虔诚,以祭祀歌颂形式,作讴歌祈祷,反映了其时人民对帝王与祖先的一种良好祈愿和敬天畏命的感情,折射出上古时代人们的心态和民俗状况,是极宝贵的民俗材料。
(三)礼乐文化价值
周代文化的鲜明特征之一,是产生了不同于前代而又深刻影响后代的礼乐文化。其中的礼,融汇了周代的思想与制度,乐则具有教化功能。《诗经》在相当程度上反映、表现了周代的这种礼乐文化,成为保存礼乐文化的有价值的文献之一。例如,《小雅》中的《南有嘉鱼》《南山有台》,均为燕飨乐章,它们或宴乐嘉宾,或臣工祝颂天子;而《蓼萧》则为宴远国之君的乐歌。从中可知周朝对于四邻远国,已采取睦邻友好之礼仪政策,反映了周代礼乐应用的广泛。又如《小雅·彤弓》,记叙了天子赐有功诸侯以彤弓,说明周初以来,对于有功于国家的诸侯,周天子均要赐以弓矢,甚而以大典形式予以颁发。相比之下,《小雅·鹿鸣》的代表性更大些,此诗是王者宴群臣嘉宾之作。“周公制礼,以《鹿鸣》列于升歌之诗。”朱熹更以为它是“燕飨通用之乐歌”诗中所写,不光宴享嘉宾,还涉及了道(“示我周行”)、德(“德音孔昭”),从而显示了“周公作乐以歌文王之道,为后世法”。除燕飨之礼外,《诗经》反映的礼乐文化内容还有:《召南·驺虞》描写春日田猎的“春蒐之礼”;《小雅·车攻》《小雅·吉日》描写周宣王会同诸侯田猎;《小雅·楚茨》《小雅·甫田》《小雅·大田》等描写祭祀先祖,祭上帝及四方、后土、先农等诸神;《周颂》中有多篇祀文王、祀天地的诗作,可从中了解祭礼;《小雅·鸳鸯》颂祝贵族君子新婚,《小雅·瞻彼洛矣》展示周王会诸侯检阅六军,可分别从中了解婚礼、军礼等。
(四)文学艺术价值
对《诗经》的文学艺术价值,后人有许多概括总结,但以对中国文化、文学的影响来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诗经》为后世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素材、题材,成为被广泛引用的“典故”。中国古代社会向来注重文学的政教功能,因而将《诗经》作为政治“经典”加以运用;周人“采时世之诗”“通情相风切”的高雅习俗积淀为借古人语言己情的表意模式;儒家“法先王”的政治观念更是直接影响了带有民族特色的征圣、宗经的思维模式;《诗经》中的大部分创作当初便是为了政教应用,编集之后便成了表意言志的恒言共语或说理论事的理论依据;经学时代的经生用之发挥儒学义理,以为其句句包含着治国经邦的大道理,句句是至理名言。其“经学之首”的地位使之成为古代学者必修必熟之课,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古代学者的政治观念、道德修养乃至文学创作。古代学者不论是说理论证,还是抒情叙事都习于引《诗》,《诗经》成为古人引用最多最普遍的典籍。先秦诸子中,《论语》记孔子言论涉及《诗经》有二十处,《孟子》记孟轲涉及《诗》有四十多次,《荀子》一书则有九十多处记述荀子引《诗》评《诗》。[14] 曹操《短歌行》一诗中竟两引《诗经》成句:“青青子衿,悠悠我心。”(《郑风·子衿》)“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小雅·鹿鸣》)。张孝祥《六州歌头》(长淮望断)——“隔水毡乡,落日牛羊下”,化用《诗》句:“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等等,不仅《诗经》的诗句成为“典故”而被普遍引用,《诗经》所表达的主题及叙事、抒情、描写的方法也积淀为富有民族特色的“模式”而被广泛继承。
其次,直接影响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创作与批评。经学是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影响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也直接影响到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与批评。《诗经》对中国古代诗歌创作与诗歌理论的影响更是重大而深远。
经学家以文学为政治工具,原本还仅仅是部分用于政教的《诗经》,在经学家的点化之下,便将部分夸大为全部,认为《诗经》篇篇句句都关涉儒家伦理道德。在《诗经》创作时代,“诗言志”之“志”十分宽泛,还是情志合一,到战国时期,“志”就偏重于“仁义”,到经学时代则是专指有关政教的儒家之志。于是,《诗经》作者以草木虫鱼等自然景物委婉言意的方法被后人归纳为赋、比、兴。在经学家眼中,“比兴有‘风化’‘风刺’的作用,所谓‘譬’不止于是修辞,而且是‘谲谏’了”[15]。比、兴是“主文而谲谏”的方法:目的是政教讽谏;方法是“引譬连类”,托物言志;效果是委婉含蓄,“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毛诗序》)。由是而被古人推崇为“诗学之正源,法度之准则”[16]。朱光潜先生说:“中国后来的诗论、文论乃至画论都是按毛苌所标的赋、比、兴加以引申和发展的。”[17]
由于《诗经》至高无上的经学地位,其所运用的赋、比、兴方法也随之身价倍增。历代政治家、诗人、文论家都极力推崇,并根据各自的政治观念、美学理想加以诠释,丰富并发展了赋、比、兴理论,使之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理论的总纲、大法,涵盖了中国古代诗歌理论的各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