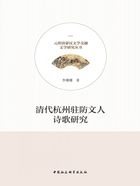
第二节 杭州驻防文人诗歌的昂扬之态
清初八旗以外族入主中原,引动了江南士人思想世界的多元裂变,进而造成文学创作的多元化。易代之际的思想涌动更易于让我们看到江南文化的承载力和丰厚度。江南是杭州驻防文学最初扎根的土壤,其中涌动的民族精神和文学力量也许从那时开始就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杭州驻防旗人。此时,京师八旗的文学创作开始呈现较为繁荣的姿态,以汉军八旗文人为主体间以满蒙文人的文学创作群体走上清初文学的舞台。旗人南下征战,一路势如破竹。征服者的诗歌与江南文人诗作中的黍离之悲不同,具有刚健昂扬、豪迈奔放的特点。旗人诗作与汉族文人诗作风格虽截然不同,但不可否认二者具有的因果关系。杭州驻防旗人属征服者,诗作风格与京师八旗诗歌风格保持了一致。
“八旗诗歌的风格主要在雄浑豪放和清旷疏俊两个方面。用笔多倾荡磊落、沉著刚隽,抒写的内容和情感也与这种笔调相适应。”[28]这一论述可谓恰切。除去部分宗室诗人因统治阶级内部倾轧诗歌具有寒意和游离姿态外,大部分八旗诗人的写作具有豪放、明朗的气概。究其原因,首先,八旗军队的勇武和节节胜利,使他们的诗歌充满了建功立业的豪迈。满洲文人顾八代于康熙年间从征云南,有诗《辛酉冬十月荡平滇南,赋赠绥远大将军赖公》云:“数载南征七出师,貔貅百万指滇池。石门槛破直擒将,黄草坝争横夺旗。”[29]清初八旗军队所向披靡,感染了八旗文人的情绪,写就的诗歌必然是激扬进取的。其次,地域文化性格的养成。八旗军队大都由北方游牧、渔猎民族组成,生活在寒冷、开阔、高峻的自然环境中,大都奔波迁徙,逐水草而生,养成了他们性格中的坚毅粗犷、朴实强悍。夏竦《论幽燕诸州》云:“幽、燕山后诸州,人性劲悍,习于戎马,惇尚气节,可以义动。”[30]文学作品是作者心灵的映现,因此清初八旗诗人的写景诗多表现粗犷的壮美。如鄂容安《山海关》云:“屹立关门压九州,两京相望划营幽。罔峦西北连雄寨,渤碣东南仰上游。”[31]汉人吴启元也写有《山海关》诗,其中“地临辽蓟中分界,天限华夷第一关。直绕长城东到海,凌空高障北依山”[32],也是呈现高旷豪迈的诗风,但却是沉重的,其中掺杂了汉族文人内心的华夷之界,因此,对关外自带一种疏离感。这应是彼时大部分汉族文人的普遍情感。最后,民族情感的注入。正如金启孮所言:“(满族)文学之作,溶入纯朴满族情感,虽一诗一词,足可见满人之思想性格,即哀感之手笔,亦流露刚健统一气魄。”[33]
雍正六年(1728)八月,以“平湖县乍浦地方,系江浙海口要路,通达外洋诸国,且离杭州止有二百余里,易于照应”[34],设立乍浦驻防水师营。雍正七年(1729)杭州驻防以“满洲、蒙古余丁及康熙六十年议裁骁骑千名内,陆续开除未尽之兵,共选八百名移驻乍浦,充水师额。拨江宁驻防八百名移驻乍浦,为水师右营,自杭州移驻者为左营”[35]。在此次移驻中,杭州驻防旗人善泰[36]调往乍浦,担任乍浦左营右翼协领[37]。他写有《自杭州移驻乍浦纪事诗》,其中展露的英豪之气和喜悦心情弥漫在字里行间。诗云:
中原无战伐,圣德应箫韶。哲后钦垂拱,苍生戴本朝。承平添武备,相度走星轺。喜气三春雨,军声半夜潮。营开新壁垒,岸泊旧旌旄。雪意西山 ,霜风六里桥。长怀盘石固,坐使海氛消。金鼓连天震,波涛入望遥。南溟飞舰舳,北斗缮招摇。有备真无患,葵心向帝尧。[38]
,霜风六里桥。长怀盘石固,坐使海氛消。金鼓连天震,波涛入望遥。南溟飞舰舳,北斗缮招摇。有备真无患,葵心向帝尧。[38]
雍正时国家政权已基本稳固。作为八旗将领的善泰有感于国家在承平时期对武装力量的系统规划,发出了赞叹。诗作充斥着快意洒脱和淳朴的英雄气,体现了此时旗人高涨的民族自信心。乍浦水师营操练场景不同于陆地士兵,善泰有《海操诗》云:“海不扬波几十秋,楼船安稳驾春流。炮声殷地三山动,何处长鲸敢出头”[39],以夸张的手法表现水师操演的震撼场面。康雍年间平湖文人于东昶有《满洲水师操》,“八旗子弟好身手,破敌弓刀说析津。海上军容船若马,谁云绝技属吴人”,赞美了八旗子弟英姿飒爽之气。此时杭州驻防旗人已不用四处征战,但仍以军事训练为主要任务。善泰作为将领,其“性情闲淡,笃好吟咏,公退之暇,葛衣紃屦,乘款段出游,臞然如山翁野叟”[40],展露的完全是一副江南文士模样。然而,康熙五十九年(1720)时他还“随征西藏,著劳绩”,说明上马征战仍是他的本职。这一特点普遍存在于八旗将领中,集军事训练与诗歌吟咏于一体,是一个“儒将”群体。
清初的杭州驻防文人诗歌创作数量虽少,但与同期的八旗诗歌共同具有昂扬向上的态势。而杭州驻防旗人作为征服者,江南地区的汉族文人则是被征服者。征服者诗歌中的昂扬与被征服者诗歌中的低沉具有互为因果的关系。此时江南文人诗歌普遍具有憔悴枯槁之音。
清军入关后,以多尔衮为首的清政权迅速平定明朝残余势力,继而占据江南。他们一路进军西南,瓦解李自成和张献忠带领的农民政权;另一路向东南进军,直取南明弘光政权。在平定江南的过程中,清兵也展开了野蛮屠杀,攻克扬州后屠城十日,随后的三屠嘉定、金华三日,无不惨无人道。清军“怀着切齿仇恨烧毁、抢劫了城市”[41]。诗人李渔在金华目睹了这一惨象写下“婺城攻陷西南角,三日人头如雨落”[42]“骨中寻故友,灰里认居停”[43]。清廷强制实行的剃发易服令更是给江南思想世界带来极大震动。顺治二年(1645)平定江南大部分地区后,清廷发布谕令:“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44]这一强制实行的民族同化政策,激起汉族人民极端反感,“宁为束发鬼,不作薙头人”是时人的普遍心声。“外来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刺激,在不断地磨合中,渐渐本土一些潜在的思想为确定自身的价值与意义,会被逐渐激发出来,并在与外来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冲突中逐渐凸显自身的内涵与界限。”[45]八旗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本就触及士大夫思想世界中“夷夏之防”的大忌,一系列不合“礼”行为的发生更加形塑了汉族文人心目中旗人的“蛮夷”形象。此时在遗民的话语世界中充斥着“神洲荡覆,宗社丘墟”“天崩地解”“裂天维,倾地纪”“神州陆沉”等礼乐荡尽的表达。遗民使用“蛮夷”“北胡”“杂种”等带有偏见性的词语指称旗人。八旗统治的严苛与江南士林精神世界的异化相辅相生,在清初几十年中上演着压制与反抗的反复。
清初江南社会的离乱和士人思想世界的激变,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舆论场”。所谓“舆论场”是指一种包含若干相互刺激的因素,从而能使许多人形成共同意见的时空环境。[46]江南文人生活在特殊的历史时空下,拥有相似的价值观念,受到时局刺激进而在共同的舆论场中进行创作,产生的文学作品大都主题相似。浙江地区的遗民群体创作更具有典型性,正如严迪昌所言:“正是这种弥漫于呼吸之间的浓重的悲凉之雾,加之该地域固有的文化学养性格,传统恪守的道德操持,所以,浙江遗民群体所显现的强项愤急、苦涩冷峭的情貌极其鲜明,每多出则饮刃溅血,凛然不返;守则穷伏山野,劲节难拔。”[47]他们诗作中的苦节哀吟大都非故作姿态,而是经历过生死磨炼的呕心沥血之作。翻检清初浙江文人诗作,映入眼帘的俱是秋虫咽露之音,如“京国烽烟满,乡关梦寐回。予怀正愁绝,何必更登台”(祝翼莘《客中坐雨》)[48],“为别语难尽,悲来情更周。是非存狱吏,生死任孤舟”(祝翼振《送开美叔赴诏狱》)[49],“不寐逢秋夜,凄清落木多。新愁排梦入,客思绕风过”(查嗣爵《不寐》)[50],“清秋忘作客,选胜不辞劳。得句题红叶,遗民问碧桃”(查嗣爵《从菩提寺历庙湾诸山》)[51],“处世多孤愤,因循病易成。洛阳空赋鹏,只恐不长生”(吴容《感怀》)[52]。此时的诗歌创作,“不啻士人的一种生存方式”[53]。遗民旧老在故国灰飞烟灭后,辗转于山水间,吟咏着风高气栗之音。
遗民行为方式及书写内容的特异在经历顺治年间的海立山飞之后,仍旧在江南社会广泛存在。如果继续推行强制措施,不但不能使遗民驯服,反而会激起更激烈的反抗,那么江南这个巨大的遗民舆论场会继续扩大,于统治必然是不利的。因而在康雍年间,统治者一方面从正面进行引导,开博学鸿词科以修史名义招纳遗民入朝。开科的原因即为“明室遗臣,多有存者,居恒著书言论,常慨然有故国之思。帝思以恩礼罗致之”[54]。此科之开,虽在遗民舆论场中又引起轩然大波,针对出与处、节与义的讨论层出不穷,但大批遗民还是以自愿或非自愿的方式接受了朝廷礼遇。这成为“汉、满之融合关纽”[55],部分地消解了遗民话语中的“狂言悖论”,收到了“揽心”之效。时人有诗作称:“此举良旷典,盛事久雍阏”。[56]另一方面,统治者开始大兴文字狱。雍正年间的汪景祺《西征随笔》案、查嗣庭诗题案、吕留良文选案,牵涉之广,惩罚之严,引起士林阶层惊惧。而获罪士人大都是浙江籍,触怒了雍正帝,四年(1726)以“浙江风俗恶薄如此,挟其笔墨之微长,遂忘纲常之大义,则开科取士又复何用”[57],停止浙省乡会试。浙江为科举大省,且科举考试是中国古代阶级升转的唯一有效途径,这一惩罚是极其严厉的。针对清初引起激烈讨论的“夷夏之辨”,雍正编纂《大义觉迷录》云:“夫我朝既仰承天命,为中外臣民之主,则所以蒙扶绥爱育者,何得以华夷而有更殊视?……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58]以拥有德行作为享有正统的标准。在康雍两朝恩威并施政策的演进下,随着时间推移,遗民逐渐淡出历史视野。
遗民诗歌哀感与八旗诗歌昂扬进取是处于同一时空、由同一事件激发的完全对立的诗歌风格。在看似对立的表象背后实则隐含着文明程度的差异。八旗诗歌从创作初始就采用汉语诗歌的形式,总体呈现较多学习、摹拟痕迹,表现的内容及感情大都具有表面的、纪实的特点。此时的杭州驻防诗歌承和了八旗诗歌特点,江南地域对其诗作的影响在随后的时代才慢慢显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