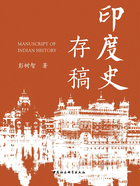
学步文稿(上)
印度近代史研究·序
编完《印度近代史研究》,掩卷沉思,许多往事,浮现在眼前。
20世纪50年代初,当我在西北大学历史系学习时,印度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和它在近现代苦难深重的殖民地地位,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每读及我国的历史,总不由得想起了邻国印度的历史。章太炎在《国家论》《印度人之论国粹》《〈中华民国〉解》和《支那印度联合之法》等《民报》上发表的文章中,关于中印两国历史与文化联系的慷慨陈词,特别是他的“推我赤心,救彼同病”“相互保持,屏蔽亚洲”“维持世界之真正和平”的话语,令人久久不能平静。我的大学毕业论文就是《近代印度的民族解放斗争》。论文是用毛笔誊清的,约15万字,现在还完整地保存在书箱里,成为我学习印度史开端的记录。
大学毕业以后,我有幸在北京大学亚洲史研究生班学习了三年。那浓郁的学习研究气氛,优越的图书资料条件,良师益友的指导切磋,加上史学界筹备1857年印度大起义一百周年纪念的学术活动,使我的兴趣几乎完全倾注在印度近代史方面。
我的第一位导师周一良先生把我及北京大学其他三位研究生一起派往东北师范大学,在教育部主办、苏联亚洲史专家瓦·巴·柯切托夫主讲的“远东和东南亚近现代史教师进修班”学习。柯切托夫老师在指导我写的《略论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义的原因》(结业论文)时的修改意见,使我终生难忘。这篇论文成为我研究生毕业论文的第一个手稿本,列入本书“学步手稿”。
季羡林老师是我在印度史学习方面第一位启蒙老师。我到北大读研究生时,周一良先生就引我去见季先生,并把我大学毕业论文的书稿给他看。在他的耳提面命的教诲下,我的第一篇印度史方面的习作《百年前印度人民起义的历史意义》,于1957年5月10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在此后关于印度近代史其他方面的文章,无不得到季老师的鼓励。进入20世纪70年代之后,季老师老当益壮的言传身教,使我更加有信心在印度近现代史领域中继续前进。《〈民报〉与印度的独立运动》,就是季老师1980年西安之行时审读的,这对大病方愈的我是有力的鼓励,是我重振探索精神的记录。
在我学习印度史的历程中,陈翰笙老师的教诲与帮助也是使人难以忘怀的。在20世纪60年代初,他在审阅我的书稿《提拉克》和《印度独立运动》时,给我提出过许多切中要害的批评,同时也给予我热情的鼓励。他在北京国际俱乐部的便宴上对我说,要勇于做拓荒者,要勤于做园丁,要甘于坐冷板凳。这一席话使我难以忘怀。后来这部书以《印度革命活动家提拉克》为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经陈老师审阅过的《印度古都德里的起义》的底稿片段和《德里和勒克瑙和章西的保卫战》幸而保存下来,收入本文集中。这也是陈老师对我辛勤培养的一个纪念。
1979年,我原想把自己1957年以来写的几十篇文章和译稿汇集成册,以纪念大起义结束一百周年。这个计划当时未能实现。三年以后,我的研究领域从印度向西亚的阿富汗和土耳其方面延伸,并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方面开拓了新的领域。虽然还在研究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史方面的问题,但重点已不在印度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感到有必要把有关印度近代史方面的文章结集成册,作为对印度近代史研究工作的一个阶段的小结。因此,汇集了这本《印度近代史研究》。
我自知水平不高,收入本文集的论文存在不少缺陷;我也自知这些论文渗透着许多师友的心血,并非我自己一人的劳动成果。有的老师,如张云波老师曾评阅过我的《1857—1859年印度反英大起义略论》一文,他已不在人世了。有许多同窗益友,如周清澍、吴乾兑、赵克毅,曾经同我合作过,现在也都改行了。管敬绪是近几年的合作者,他最近也搞法国史了。但是师友们的指教和支持,是我永志不忘的。此外,为了誊抄文稿,许多老师、研究生和大学生花去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在此一并向他们致谢。
本文集中的文章基本上按发表时间先后排列。在同一时间内,则按问题归类。文章保持原来面目,誊抄时只在译名、马列主义著作引语方面做了少许修改,对文后赘语做了删除。读者只要从历史观点去看这些文章,就不会对前后出现的重复、矛盾以及其中偏颇之处感到奇怪了。
本书稿承季羡林老师过目正谬,谨致谢意。
彭树智
1982年1月10日于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