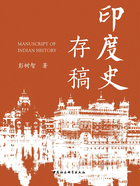
前言:《印度史存稿》的往事与回忆
2021年7月中旬,是一个往事与回忆的时刻。当时,我从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韩志斌的电话里,听到两个消息:一是从网上购得我在1982年编写的《印度近代史研究》手稿一部二册;二是西北大学南亚研究所正式成立。
第一个消息使我颇感意外。当时我怎么也想不起有这部手稿,及至看到所里寄来此稿的复印件之后,一桩桩旧事才逐渐如剥茧抽丝般地浮现在眼前:原来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的科研生长点由南亚转移到中东以后,为了总结印度史研究成果而编了这部文集。书稿送到出版社,被推说书稿找不着了,拖了很长一段时间不给回音。后来提出出版我另一部书稿《现代民族主义运动史》[1],并答应继续寻找失落的书稿。当时我的行政工作,以及教育科研事务繁忙,无暇追索原稿,时间一长,便淡忘了。时隔近四十年之久,加上我已年过九秩,对此事真是失忆了。现在重新目睹它残破的旧貌,第二册缺最后几页,第三册荡然无存,心中不禁悲怆。幸好第一册原来目录尚在,终于恢复了原貌。通览全稿,感慨万千,久久不能平静。昔日笔耕学步劳作,失而复得,成为个人学术史上一段逸事。《老子》第三十八章有“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的名句。按杨公骥先生的解读,把“不德”释为“不得”,认为上等的德、最高尚的德不认为自己有得,因此是真正的“有德”;而下等的德唯恐失去德,因此无德。得与失的这种辩证解读,确有点哲理了。这真使人想起“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句老话;也令人感慨于“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这个初有失而终有所得的典故;更使人有悟道于本“书稿题辞”中,关于“存在”与“成性存存”的禀始存终的人类文明交往历史观念。我在敝帚自珍的同时,心中充满了对中东所为此事而辛劳的诸位同志的感谢之情。
第二个消息令我兴奋不已。看到那批复成立西北大学南亚研究所的“红头文件”复印件,真有一种“踏花归来马蹄香”“一日看尽长安花”那样诗意惬心的感觉。回忆自己的学术生涯,正是从世界史、亚洲史、南亚史,而后进入中东史的路径行走过来的。我对《印度近代史研究》书稿自序中下述话感到特别亲切:“当我在西北大学历史系学习时,印度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和它在近现代苦难深重的殖民地附属地位,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东西方文明交往的历史观念,开始在我的思考中萌生。当时,倡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侯外庐校长,用他从事中国思想史的体验告诉大学生说:有志于从事学术研究的青年,从进入大学校门起,就要有意识地选定和不断培育自己的科研生长点,以便在实践中根深叶茂、开花结果。这些话伴我终生,无论是逆境顺境,无论遭遇多大变化,无论社会大环境如何变动,我都会记住“培育科研生长点”这个理念,以科研为志业,坚定、坚持、坚守历史本位,矢志不渝。从1950年进入大学到1986年国务院学位办批准“世界地区国别史·南亚中东史”博士点,从历史系、文博学院和中东研究所,我都一直努力把南亚、中东和中亚地区联结成一个研究整体。今日以中东研究为主体、以南亚和中亚为两翼研究格局已经应运而生,昔日梦想的世界地区型研究体系已经变为现实。回首往事,展望未来,真的令我这个已跨过了九十岁门槛的老学人兴奋不已。
两个消息,双喜临门。这既是印度史稿的回归,又是对南亚研究所成立的一份献礼。我思考用《印度史存稿》为书名,以表示它的历史档案性价值。为了使它有完整性和系统性,我又省视书箧,翻阅归存,竟然又有新的收获。我发现了另外两件印度史方面的写作手稿,可作为《印度史存稿》的组成部分,使其内容更丰满,时间顺序上也有上下线索可循。
首先,这就是《略论1857—1859年印度反英大起义的原因》手稿。它是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的组成部分,是1957年4月14日我在东北师范大学教师进修班写的“结业论文”初稿。其缘由是这样的:新中国成立伊始,首先要处理好与所在的亚洲地区各国关系。1954年,北京大学招收亚洲史研究生,我因有《近代印度的民族解放斗争》毕业论文,被推荐保送入学,师从周一良、季羡林二位导师。后来,教育部在东北师范大学举办“远东和东南亚近现代史教师进修班”,由苏联专家瓦·巴·柯切托夫主讲。北京大学把我们四个研究生派到该班学习。这样,我在西北大学、北京大学之后,进入东北师范大学。我的研究生论文由柯切托夫和张云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调来辅助专家工作)为指导教师,采用教师进修班“结业论文”的形式。柯切托夫老师对我说,中国没有实行研究生学位制,但你是北大的亚洲史研究生,我就按苏联的副博士要求,指导你写作和论文答辩。保存到现在的《印度民族大起义原因》的手稿评分上,两位导师都给了“伍分”[2]的满分。此稿被译成俄文,是亚洲史教师进修班唯一进行答辩的结业论文。柯切托夫老师在答辩会上,亲切地用俄罗斯民谚“奶酪味美,再烤一下味更佳”来鼓励我进行再修改工作。后来,经过全面修改的《1857—1859年印度反英大起义前夜的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发表在《西北大学学报》1957年第3期上,其中也转述了结业论文中的一些论点。同样,《1857—1859年印度反英大起义略论》也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1957年第4期上。这些文章有些地方看似重复,其实因时间不同,论述重点不同,作为学术史的档案性资料,有必要把它作为往事与回忆的手稿以及研究路径的寻根溯源方向,加以保留。其次,是《近代印度民族解放斗争》手稿,是大学时代的稚嫩之作,让它只在本存稿中保存其封面和部分目录,作为纪念。手稿已捐赠西北大学图书馆,作为馆藏保存。
此外,《印度史存稿》中保留了《印度革命活动家提拉克》和《阿富汗三次抗英战争》这两篇文章。提拉克是继印度大起义和启蒙运动之后民族新觉醒时期的代表人物,1958年我在《历史教学》杂志上发表了《提拉克——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伟大先驱》一文。后来被《外国历史小丛书》主编陈翰笙先生注意到,因此约我写了《印度革命活动家提拉克》。陈先生是位有世界史眼光的学者,他也关注培养人才。他和季羡林先生都是我学习印度史的业师。在20世纪40年代,他在印度工作过,用英文出版过有关印度社会经济方面的著作,被列入美国Who's Who名人录中。他还有《印度和巴基斯坦经济区域》一书,其中在地区国别史中自然条件与合理制度之间关系问题上,提出了“制度是关键因素”观点,至今不失为真知灼见。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名誉所长,关心科研队伍建设,致力于提高青年学者英语工作水平。他在《百科知识》杂志上,看到我写的《1841年阿富汗人民反对英国侵略者的斗争》一文后,便约我为《外国历史小丛书》写一本《阿富汗三次抗英战争》。他在来信中讲了三件事:第一是《外国历史小丛书》重在普及,但不忽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气派世界史体系的建设方向,无论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制度方面的选题,都要围绕这一思路进行;第二要重视大众化普及世界史知识、提高世界史意识工作,培养青年历史学者既可以“专深”,又能“浅出”的面向广大群众的能力;第三是把印度和阿富汗综合研究引向深入,因为印度是英帝国侵略扩张的大本营,阿富汗是印度、中国、中亚、中东地区性的“十字路口” “兵家必争之地”。这封信写于苏军入侵阿富汗,而我国学界正处于“西线无战事”沉默状态。正是在陈老师的启发下,我把学术生长点由南亚转向了中东。为反映这一段学术史缘由,我特意把《印度革命活动家提拉克》和《阿富汗三次拉英战争》作为“学步书稿”,编为一集,列在“学步文稿”之后。
回忆是人类大脑思维活动,也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大脑的记忆,如何产生,如何重现问题,成为2021年世界十大科学前沿问题之一。在写这篇前言时,我想起了美国学者J.W.汤普森在《历史著作史》中的一段话:“历史和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比通常设想得更为密切。因为一切历史和一切科学归根结底都是思想。”正是这个“一切历史”和“一切科学”的思想,是存在的根源真谛和把回忆的东西内化为“思想”,使内在事物在可能性中相遇与回归。这就是黑格尔“巨大历史感”所归纳的“回归历史,获得自觉”,也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用唯物史观这一科学思想把历史归结为自然史和人类史统一互动交往的、人类解放的“历史科学”。
唯物史观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是用历史原则,提升哲学本体论而对存在论的创造。它是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按照“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来确证存在的。正因为如此,也使我在《印度史存稿》原稿最后两集中收录了有关甘地在民族主义思想的回忆笔记和资料。甘地民族主义思想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历史问题。我从学术学步之日起,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把研究较成熟的思想,集中写入《东方民族主义思潮》一书中。当时研究的重点,是把甘地民族主义思想放在亚洲非洲,特别是在南亚中东地区的中观研究视野,比原来国家微观研究要广深一些。[3]由于这个原因,我删去了原稿中这两集,仅保留了《论甘地的非暴力抵抗运动》一文,并将它列入“学步文稿(下)”之中。现在看来,应当从“历史转变为世界史”的人类文明史发展新时期思考,更应当从人类文明交往的历史观念贯穿其中为“通观”思考。这使我想到印度学者D.P.辛加尔在《印度与世界文明》一书中的话:“在今日印度,印度教徒从那些与其祖先最初提出的相差无几的概念中寻求灵感。在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语言与文学方面,远比甚至希腊和意大利这一切更有连续性。”也正如印度哲学家拉达克里希南所说:“对印度教徒来说,宗教是心灵的体验或心志。它不是一种想象,而是一种力量;不是一种理论命题,而是一种生活的信念;宗教是对基本现实的感知,而不是一种关于神的理论。”[4]
最后,对往事与回忆,要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切都随着时间、空间、人间这“三间”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回忆是从微观细节开始的,它往往会给人以具体难忘的初始印象。我个人的体会,有一个日子记得特别深刻,那就是1957年5月10日。这一天,《人民日报》第二版发表了我写的《百年前印度人民起义的历史意义》。这对我当时作为一名只有26岁的研究生而言非常难忘。尤其令人难忘的是,在该报还发表了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杨人楩老师呼吁重视世界史的文章,他提出“如果排队,不妨把世界史排在末尾”,但“不要把它抛在外边”。此二文见报后,北大世界史研究生齐文颖师姐后来告诉我说,当天北大十九斋(研究生楼)“像过节日一般欢腾起来”,同学们似乎“听到了世界史学科发出的未来希望的最强音”。当时,北京大学的四位亚洲史研究生,被周一良老师派往东北师范大学,随苏联专家柯切托夫主讲的“远东和东南亚近现代史教师进修班”学习。柯切托夫老师在第一时间把《人民日报》5月10日发表《百年前印度人民起义的历史意义》的事情告诉我,祝贺之外还说《人民日报》如同苏联《真理报》一样,许多学者一生都难得在其上发表一篇文章。我把它列为本书“学步文稿(上)”的首篇,是因为它是我终生难忘的学步第一个路标。说也凑巧,直到半个多世纪之后,即2015年6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我的《人类文明交往的历史观念》一文时,又引起了我对1957年5月10日这一天的回忆。
《印度史存稿》有说不完的往事与回忆。整理这部文稿工作把我的思绪带回到大学时代。那时我对学历史不大感兴趣,记得在大学入学考试的国文试题《我的志愿》中,我倾诉了自己对文学的爱好。然而,正像一句外国成语所讲,历史最喜欢同人开玩笑,你本想走进这间房子,它却把你引进另一间屋里。我因为历史考的成绩优秀而被历史系录取。失望之时,中学语文老师潘子实先生用“文史不分家”来鼓励我学习历史。这时,一个儿时的问题又浮现脑际:为何一个勤劳智慧的文明古国,而且地大物博的中国却在近代以来老受别国欺侮?我学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历史,尤其是邻邦印度的历史,和中国都是相同的命运。这个不解之谜使我想从世界近代以来的历史中找答案。有一次我读《民报》这个革命民主派刊物时,发现中国和印度两国革命志士同病相怜、志同道合的交往情形,令人感动。正在此时,侯外庐先生被任命为西北大学校长。他在西北大学关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也关心青年史学人才的培养。他有一句话使我受用终身:“一个有志于史学的大学历史系青年,一入学就要确立学习的大方向和找好学术的生长点,然后在这里努力学习,生根、开花、结果。”正是在这种条件下,我选定了世界史的“大方向”和印度史的“生长点”,后来又转移到中东地区国别史方向,形成了人类文明交往历史观念,结果在历史专业上,使之成为我终生的“志业”。
在编校这部书稿时,我又一次领悟到存在、人生、生命和人类文明交往自觉历史观念的意义,也进一步领悟到人文精神的真谛。在编校本书稿的过程中,我也在思考《京隐述作集·哲以论道》和《掌文日书》的修改工作,并且为王泰写了《以信代序:人类文明交往中的历史自觉》的万言长序。那是王泰以他《近代以来埃及宗教与政治关系的历史考察》这五十多万字著作成书后,在祝贺我九十岁生日时提出的一个请求。我做到了写序和编校两不误,而且谈论的是同一话题。
我喜欢黑格尔的“回归历史,获得自觉”的哲学命题,更喜欢恩格斯的“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的历史自觉意识。的确,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比其他任何一个先前的哲学派别,甚至比黑格尔,都更加重视历史。”我在《京隐述作集·史以明道》卷首叙诗中有“万物皆有史,物始物终史伴随”之句,的确,“历史自觉”是人类最根本的自觉。我由一个爱好文学的青年而在大学时代走进了历史学这个人类文明交往的科学大厦,应当为此而庆幸没有辜负此生。这个历史的偶然性促成了我的人生成为以历史科学为“志业”的劳动者的一生。我获得过许多教学和科研奖,但最看中的还是1986年9月教师节被授予的“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称号和“人民教师”奖章。我总是忘记自己的生日,但忘不了每年众多学生在教师节对我的问候。教师节成为我劳动栖息于大地上最快乐的节日。在“前言”的结语处,我谨奉献上自己初始学步的《印度史存稿》练笔之作,并且以九十一岁老学人夕阳般微弱的光和热,与西北大学中东、南亚、中亚科研群体一道,为中国、世界、人类文明交往事业,努力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人为何物?人是制造工具并使用工具进行劳动来创造文明的高等动物。写好一撇一捺的“人”字,是人之为人的根本人格。这也是劳动者思维的价值观和团结协作的关键思维属性。人类文明交往的历史观念,其人文精神就在协作劳动、团结奋斗的真谛之中。我深深感受到,把人生的劳动贡献,定位于人类文明史上,而不是名呀、利呀、位呀那些都应当淡然处之的东西。
谈到人生,我觉得理应坚持诚实劳动创造世界的人文精神,坚守勤奋、严谨、求实、创新、协作的科学态度。对于我自己,最重要的是,顺乎自然,乐度晚年的心理状态。在正在修改的《掌文日书》中,我把“顺乎自然”具体化为人生盛开的诗意栖息“六然之花”:
西望长安远,面对京华,心境坦然,生活恬然,开心怡然。活好每一天,生机盎然、自然。死亡来临时,如花片落地,轻盈飘然!
同样,在正修改的《掌文日书》中,我把“六然之花”植根于“开劳动花、结文明果”的“六有之果”当中:
有理论的学术,有方法的探研,有创新的继承,有接力的群体,有结果的开花,有诗意的人生。
勤劳的小蜜蜂,尚且以本能采百花汁,以酿自己的蜜。落花生花落之后,根下犹结成串果实。贵为文明创造者的人类,更应发挥主动性、积极性和自觉性的人文精神,以“人文而明之”“人文而化之”的文明文化劳动,为新的文明形态添砖加瓦。在这里,我用《老学日记·题史》以结束本前言:
爱自然,为人类。自然育人,人化自然。自然史,人类史,历史科学双轮互动,弘扬人文精神,在文明交往大道上,共同追求真善美。
彭树智
2021年10月28日初稿,2022年12月29日定稿于北京松榆斋
[1]《现代民族主义运动史》,1987年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将摘要作为《世界史·现代卷》第七章。该书为齐世荣教授主编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2]当时是学习苏联的五级评分制:三分及格,四分良好,五分优秀。这里的“伍分”,比楼公凯教授给我大学毕业论文《近代印度的民族解放斗争》的“玖拾分”还要高,真令我兴奋不已。
[3]在《东方民族主义思潮》的“南亚的民族主义与政治文化”一编中,较系统地探研了甘地民族主义的政治文化特征,对甘地的政治、经济、社会观,对其宗教道德型民族主义思潮体系进行了分析,可同本书的论述对照参考。参见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二版,第87—155页。
[4]印度教是印度文化之根。西北大学中东南亚史博士梅晓云有《文化无根——以V.S.奈保尔为个案的移民文化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著作,其中论“奈保尔三角”(特立尼达—英国—印度)论点,值得文明交往研究者深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