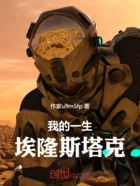
第33章 NASA(1961)
1961年秋,加利福尼亚州,帕萨迪纳。
空气里漂浮着桉树焦糊味,喷气推进实验室的混凝土墙面上还残留着三周前“探险者一号“发射失败的烟痕。
冯·布劳恩的手指在喷气推进实验室的访客簿上停顿。泛黄的纸页间,“Qian Xuesen 1943-1949“的签名正在褪色,像枚被遗忘的火箭弹道。
“他本该在这里见证卫星升空。“凯斯·格里南用麂皮擦拭着JPL创始铭牌,1943年的青铜铭文在洛杉矶的雾霾里泛着青光。走廊尽头传来闷响,先锋TV-3火箭的燃料阀又在试验台炸裂,四氯化氮的刺鼻气息顺着通风管道涌来。
就在几天前,艾森豪威尔总统签署了《美国公共法案85-568》(United States Public Law 85-568,即《美国国家航空暨太空法案》),创立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其职责扩展到航天领域,包括天文学和地球科学。凯斯·格里南被正式任命为NASA首任局长,而冯·布劳恩则被任命为马歇尔太空飞行中心总指挥。
镁光灯下,新任NASA局长接过任命状时,指尖还残留着先锋火箭泄漏的偏二甲肼触感。而在阿拉巴马州的马歇尔中心,冯·布劳恩的委任函正被军机押运——中央情报局用红铅笔在“前纳粹党员“的备注栏打了十七个问号。
不同于科班出身、根红苗正的凯斯·格里南(时任俄亥俄州凯斯理工学院院长,二战时期是美国海军水下声学实验室主任),冯·布劳恩的人生经历堪称传奇。
出生于普鲁士贵族家庭的他,在柏林工业大学机械工程系毕业后加入德国陆军火箭研究组,1937年成为佩内明德火箭研究中心技术总监,二战期间主导开发世界首款实用弹道导弹V-2,成为纳碎德国的大杀器,组织生产超3000枚,其中约1400枚攻击盟军目标。但后期因反对将火箭研发完全军事化与纳粹产生矛盾,并1946年移居美国,是二战时期首屈一指的火箭专家。
但眼下,这两位NASA的奠基者和创始人却在郁闷的彪着脏话。
“他们管这叫忠诚测试?“冯·布劳恩捏扁咖啡杯,“钱在加州理工带出的学生正在莫斯科帮科罗廖夫算轨道!“他突然抓起加密电话:“告诉国防部,如果再不解除华裔科学家的保密分级,我就把土星五号图纸寄给BEIJING!“
凯斯·格里南没有反驳,而从档案室拖出蒙尘的蓝盒子,1945年的黑白照片上,钱正为冯·布劳恩讲解V-2的泵压系统,两个来自敌对国家的天才在美军监视下共享计算尺,这是只有在美利坚才会出现的画面。
可惜的是,现在已经成为了仅有的回忆。
“知道钱离开前留下了什么吗?“凯斯·格里南抖出张皱巴巴的公式纸,“超音速燃烧冲压发动机的雏形,现在却锁在五角大楼的红色禁区。“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如果不是一年前苏联抢先造出了卫星,华盛顿那帮官僚绝不会让我主持这项工作,就像1年前钱的遭遇一样。”冯·布劳恩一边看着《华侨日报》的英文版一边抱怨道。
只见头版头条赫然是:钱在清华园挂出“喷气推进研究所“的牌子。
这时,总统专线不合时机的响了起来。
“冯·布劳恩博士,肯尼迪总统想询问一下卫星发射进度。”肯尼迪特别助理官僚式的声音传了过来。
“能否转告总统先生,“冯·布劳恩针锋相对的说道,“你们在1950年驱逐了能让我们提前四年发射卫星的人,现在却质问为什么苏联的狗都在太空拉屎?“
......
圣诞夜的暴雪封锁了卡纳维拉尔角,JPL废弃B区传来档案员的惊呼。半本笔记在铅酸电池箱后泛着幽蓝,钱的钢笔字穿透辐射尘清晰可辨:
“三级火箭分离频率必须规避14.7Hz箭体共振...“冯·布劳恩冲进控制中心时,雷神-艾布尔火箭正在发射架癫痫般震颤,德国人的咆哮震落了雪茄灰:“上帝啊,他连液体晃动阻尼系数都算好了...难道上帝要收走所有火箭专家吗?“
当那张泛黄的计算纸贴上控制台,液体晃动阻尼系数在示波器上画出完美正弦波。
大西洋上空的电离层折射着奇异辉光,监控屏雪花点里浮现出1950年听证会场景:钱学森在西服第三颗纽扣处别着加州理工校徽,身后FBI探员的阴影如火箭尾焰般拉长,吞噬了所有关于宇宙的答案。
火箭升空的气浪震碎控制中心玻璃时,凯斯在漫天纷飞的保密文件中,瞥见钱学森1949年未寄出的信笺残片:“...若计算无误,多级火箭理论应能支撑起星际旅行的骨架,可惜我们终将活成分母...“
与此同时,中国,大西北。
钱学森放下被汗渍浸透的眼镜,试验场炽热的阳光把发射架的铁皮烤得发烫。他望着远处被风沙模糊的地平线,忽然想起三天前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
“参数被篡改过。“林之恒的指节在计算尺上泛白,老式台灯在图纸上投下摇晃的暗影,“燃料混合比明明是2.35:1,这个系数...“他的声音戛然而止,铅笔尖在计算纸上戳出深痕。
钱学森的手指突然停在某页图纸上,他的瞳孔突然收缩。那页图纸的右下角,原本应该空白的边角处,竟有一串极浅的俄文批注——“当燃料泵转速超过5000转时,需要重新校准压力参数“。
试验场临时会议室的灯光在深夜两点依然通明。钱学森推开沾满咖啡渍的计算纸,指着某个方程式的第三项:“这里,压强换算系数应该是1.05,不是他们标注的1.5。“
他的钢笔尖在图纸上戳出一个小洞,“苏联专家故意调换了这个参数。“
凌晨四点,西北风呼啸着穿过导弹试验场的铁皮工棚。钱学森突然抓起桌上的计算尺,在月光下飞快地划出新的轨迹线。当第187次计算结果显示弹道误差值终于缩小到0.01%时,他猛地推开窗户,让戈壁滩的冷风灌进办公室。
“点火!“随着指挥员的嘶吼,发射台瞬间被白色烟雾笼罩。东风一号的尾焰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划出一道刺目的光带,林之恒的手表秒针在剧烈震动中咔咔作响。
当导弹最终在300公里外的预定靶区炸开蘑菇云时,钱学森发现自己的笔记本已经被汗水浸透了整整三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