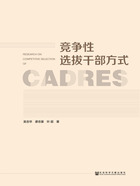
导论
一 研究背景
“竞争性选拔干部方式”是指面向社会或在本单位、本系统内部通过公开、竞争方式选拔任用干部活动的统称,包括面向社会的“公开选拔”、在本单位或本系统内部进行的“竞争上岗”以及其他一些在实践中出现的竞争性选拔干部形式。2009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完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的论述中提到“完善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等竞争性选拔干部方式”,这是党的权威文件首次提出“竞争性选拔干部方式”这一命题,并将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等具有公开性、透明性、考试性、竞争性等特点的干部选拔任用形式统称为竞争性选拔干部方式。
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竞争性选拔干部方式迄今已经历了30余年的发展历程,其形成与发展有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的动态背景。以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主题的政治体制改革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的相关诉求,是竞争性选拔干部方式形成的宏观背景;持续不断阶段性推进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是竞争性选拔干部方式发展的中观背景;而作为干部人事制度首要环节的选拔任用方式改革,则是竞争性选拔干部方式产生的直接背景。反映政治体制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诉求的选拔任用方式改革的主要动因是,于革命战争年代发展并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大一统干部委任制,在改革开放之后日益显露出其任用方式单一、选拔视野狭窄、不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选拔任用过程缺乏透明度等制度弊端,以及在选人用人实践中存在的任人唯亲、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作为突破大一统委任制的一种选人用人新方式,探索和推行竞争性选拔干部方式,就是期望解决传统干部选拔任用的问题及弊端。
从全国各地各部门探索和推行竞争性选拔干部方式的实践来看,这一干部选拔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达到预期目的和成效。换言之,对于克服大一统委任制的弊端,扩大选人用人视野,抑制干部选拔任用中的腐败和不正之风,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均取得了一定成效。中共中央组织部委托国家统计局在全国范围所做的民意调查显示:2008~2012年五年间,公众对防止和纠正用人不正之风的满意度提高11.24分,选人用人公信度提高11.26分,对组织工作满意度提高6.39分。[1]本研究于2014年2~6月对公众、参加过竞争性选拔活动的职位竞争者以及组织人事部门干部的调查显示:公众、职位竞争者和组织部门干部比较一致地认为竞争性选拔干部方式提高了选人用人公信度,且绝大部分公众、职位竞争者和组织部门干部认为,竞争性选拔干部方式有利于选拔优秀干部和抑制不正之风。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在推行竞争性选拔干部方式的实践中,亦出现了一些大大小小的问题。一是适用范围扩大化。不少地方在实践中把竞争性选拔作为干部选拔任用的主要方式甚至唯一方式,对选任制、委任制、聘任制等不同类型的干部选拔任用“一刀切”式地采用竞争性选拔干部方式。二是选拔效度的“高分低能”现象。考试本身的局限性、“应试”文化的干扰等多方面原因,导致竞争性选拔干部中部分胜出者存在“考分高、能力弱”的情况。三是竞争性选拔干部方式的制度供给缺失。竞争性选拔干部方式与常规委任制关系缺少法规界定,实体制度规范过于笼统,配套制度供给不足,与干部管理的相关制度缺乏衔接。四是缺少科学和先进的技术方法。“德”的测评缺乏具体指标及量化方法,资格条件设定缺乏职位分类和素质框架依据,基于经验的实践创新有待于进一步科学化提炼。
竞争性选拔干部方式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这些问题无疑需要进行反思、研究和规范。201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完善竞争性选拔干部方式”的要求;[2]2013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关于完善竞争性选拔干部方式的指导意见》,要求合理确定竞争性选拔的职位、数量和范围,竞争性选拔要坚持实践标准、实绩依据、实干导向,不能只看分数;[3]2013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改进竞争性选拔干部办法”,“区分实施选任制和委任制干部选拔方式,坚决纠正唯分取人、唯票取人等现象”。[4]2014年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在明确规定“公开选拔、竞争上岗是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方式之一”的同时,针对存在的问题,从合理确定范围及适用情形、资格条件设置、加强组织把关、提高竞争性选拔科学化水平等方面做出了规范性规定。[5]这些要求和规定,既说明了竞争性选拔干部方式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同时亦为改进和完善竞争性选拔干部方式的研究提供了指导性思想。正是在此背景下,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发布的《201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指南》中设定了“完善竞争性选拔干部方式研究”这一选题,我们基于研究领域的相关性及研究专长而申报了指南中的该选题并获得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