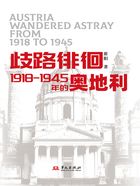
第三章
动荡的二十年代(1920—1929年)
一、“国联殖民地”
1920年10月1日,奥地利国民议会通过了新的宪法,这就是几经修改、断断续续一直沿用至今的“1920年宪法”。这部宪法规定奥地利为联邦制国家,联邦总统为名义上的国家元首。议会实行两院制,国民议会(下院)的议员由全国直接选举产生,拥有立法、弹劾总统等重要权力,政府需要对国民议会负责;联邦议会(上院)由各州选派代表组成,对国民议会的决议只具有延期否决权。由于政府总理一般都从国民议会的多数党中提名,因此哪个党派控制了国民议会,就等于掌握了奥地利的最高权力。
第一共和国时期,奥地利的两大政党分别是成立于1889年和1891年的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社会党。前者信奉社会民主主义,受工人阶层支持,首任总理卡尔·伦纳和外交部长奥托·鲍威尔皆出自该党;后者秉持奥地利传统的天主教精神,代表教士和广大乡村农民阶层的利益,领导人是伊格纳兹·塞佩尔。奥地利刚独立时,社会民主党一度在政坛独占鳌头,1919年2月议会选举后成为多数党。除了民族统一和经济利益等理由,社会民主党认为一个更大的德意志国家有助于巩固民主制度、增强该党的势力,因此积极推动德奥合并。但巴黎和会上的失败和《圣日耳曼条约》的签订使社会民主党受到了不小的挫折,1920年10月其多数党的位置就被基督教社会党取代了,伦纳、鲍威尔等人也相继辞职。此后直至1934年5月,基督教社会党长期处于执政地位,奥地利总理也几乎全部是基督教社会党成员(唯一例外的是与基督教社会党关系密切的约翰内斯·朔贝尔),社会民主党则是最主要的反对党。其他中小政党还包括大德意志人民党、农民党、保守人民党等,它们的力量有限,经常与上述两大政党缔结联盟。

1978年奥地利发行的纪念社会民主党创始人维克多·阿德勒的邮票
德奥合并既然已不可行,眼下奥地利无论是由哪个党派执政,最迫切的任务都是应对千疮百孔的经济烂摊子。“一战”对奥地利本土的破坏并不严重,战后国内也没有爆发革命,社会秩序总体比较稳定,但奥地利经济恢复的速度却远逊于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等邻国。究其根源,是奥地利旧有的国家经济结构遭到了根本性破坏。
奥匈帝国实行明确的地区专业化生产制度,波希米亚集中了大量的工业部门,匈牙利负责生产粮食,奥地利则以贸易和金融业为主。以往,奥地利和匈牙利都曾试图扭转本地过于单一的经济格局,却没有成功。奥匈帝国解体后,这种分工模式的弊端立刻给奥地利造成了致命伤害。帝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工业生产能力留在了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不得不重新规划工业基础建设,但进度因受资金匮乏、人才不足、原材料短缺等的影响而一拖再拖。奥地利的农业规模也很有限,只能产出一些甜菜、小麦和马铃薯,70%的粮食要依赖国外进口,这是造成1918年冬季全国性食品危机的主要原因。至于奥地利擅长的对外贸易领域,情况就更糟。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等邻国为了实现经济上自给自足和防范奥匈帝国复辟,纷纷设置了极高的关税。奥地利各类贸易品中,只有奢侈品和纺织品的出口情况略好一些,但于大局无补。一些痛心的奥地利人哀叹,丧失了经济腹地的奥地利是“一侧与大海无缘,另一侧被关税壁垒阻隔”。
1921年2月,刚担任英国殖民地事务部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在向英国内阁呈送的一份备忘录中提出:“奥地利的经济毫无起色,必须依靠大笔外国贷款才能维持运转。如果想让奥地利存在下去,就得尽快改善其政治和经济处境。”事实上,从1919年到1921年,英、法、美等国已经先后贷款给奥地利2500万英镑,但西方大国不可能像慈善家一样持续为奥地利输血。丘吉尔了解奥地利经济的症结所在,为此他提出了允许奥地利与德国合并、组织“多瑙河邦联”或同周边国家建立关税同盟之类的经济组织等几条出路。但丘吉尔清楚,他的建议无一例外会遭到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反对,基本没有可操作性。3月,英、法、意、日四国共同为奥地利开出了一剂全面复兴经济的“药方”,内容有改革内政、明确贷款用途和设立监督机构等。起初四国自信地以为,只要应对得当,奥地利经济有望在短期内走出谷底,但由于高估了奥地利的金融信用基础,仅3个月后,这个计划就被证明不切实际。
1921年6月21日,前维也纳警察局长、无党派人士约翰内斯·朔贝尔出任奥地利总理。他一面批评奥地利议会中的许多议员“总是个人利益当先,党内小团体利益其次,党派利益第三,而把奥地利的利益置于最末”,号召各党派团结一致、共渡难关;另一面请求英美等国尽快出手相助:“奥地利离开英国和美国的援助将无法生存。我们没有煤炭,也没有原料,要是两国能为我们供应这些恢复生产所必需的物资,五年后就可以救活奥地利了。”朔贝尔还恳请英美两国提供长期贷款、协助稳定奥地利克朗的币值。他说:“我将任命一位值得英美两国信任的财政部长。此人不是银行家,而是一位知识渊博、诚实可靠的实干家和专业人士;不是忠于某个党派的政客,而是一位爱国者。他不会总待在维也纳的办公室里,而是要到伦敦和华盛顿去,向它们证明奥地利能够、也必须生存下去,而且将会骄傲地回报那些曾帮助过他的朋友。不要忘记奥地利是个新生国家,它的自然资源还没有得到充分开发,水力也要在10年后才能代替煤炭。到那时我们的工业产能就可以得到充分释放,更何况我们还有一大批出色的知识分子和熟练工人。给我们时间、给我们信任、给我们贷款,奥地利将在欧洲国家中扮演重要角色。”
但还没等朔贝尔这一大段慷慨陈词收到回复,奥地利的通货膨胀已近乎失控,克朗急剧贬值至战前的一万五千分之一。心急如焚的朔贝尔“病急乱投医”,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缔结了《拉纳条约》,以正式承认苏台德地区是捷克斯洛伐克领土为代价,换得一笔急需的大额贷款。一向精细的朔贝尔这回犯了个大错误——苏台德的归属当时是一个高度敏感、不能轻易触碰的政治话题。在1918年之前的数百年里,苏台德地区一直是奥地利领土,居民也绝大部分说德语。“一战”后,协约国将苏台德地区划归捷克斯洛伐克的做法明显缺乏历史和现实依据,早已令奥地利人十分愤慨。果不其然,《拉纳条约》立即引发了奥地利国内民众的一片哗然,社会民主党、大德意志人民党等党派也趁机群起攻之,抵挡不住的朔贝尔只好在次年5月黯然辞职,重新回去当警察局长了。
继任总理的塞佩尔吸取了朔贝尔的教训,把克服经济危机的希望再度寄托于国际联盟。1922年9月6日,塞佩尔在国联理事会上向各国求援,说奥地利的经济危机绝不是一个孤立问题,若处理不当会危及欧洲和平。他还诚恳地表示,奥地利愿意承担必要的义务。国联理事会讨论后同意了塞佩尔的请求,责成英国、法国、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四国与奥地利组成特别小组委员会,研究改善奥地利财政的方法。10月4日,塞佩尔代表奥地利政府与上述四国签订《日内瓦议定书》。该议定书详细地列举了援助奥地利的各项具体措施,包括由国联理事会出面保证奥地利财政实行国际监督、奥地利恢复金本位货币、设立新的中央发行银行、实现国家预算收支平衡等。作为交换条件,塞佩尔答应将德奥合并禁令再延长20年,即奥地利在1942年以前不寻求与德国合并。四国随即向奥地利提供6.5亿金克朗的贷款。国联还任命财经专家、荷兰人齐默尔曼为特派员,赴维也纳监督奥地利的财政状况。齐默尔曼的工作卓有成效,到1926年6月30日,奥地利财政颇有改观,新发行的货币先令以1:10000的比率取代了原来的克朗,金融信誉也基本得到重建。国联的援奥计划顺利结束。
塞佩尔签订《日内瓦议定书》本来是一桩利国利民的好事,但奥地利舆论和许多民众却偏执地认为,将本国经济置于国联管辖下的做法损害了国家主权,使奥地利成了“国联殖民地”。再加上国联未能按计划在1924年底之前完成奥地利的经济整顿,只能将监督期限又延长了两年,塞佩尔为此饱受质疑,最终和两年前的朔贝尔一样被迫引退。一面是崩坏的经济形势,一面却对接受外援心怀不满,说明大多数奥地利民众还没有从昔日帝国的迷梦中清醒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