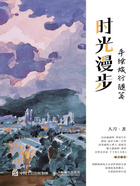
我们穿过人群走到路边一起画画
大三暑假,我到北大创业基地谈合作项目,顺便见了画友炒饼。
和炒饼相识纯属偶然。有一天我看到炒饼的主页,他每天都会分享自己的钢笔速写绘画作品,内容多是小区旁边的公园、咖啡馆、博物馆写生等。当时他在画小区门口的大树,连着发了好几条带着猫坐在小区门口写生的照片。我觉得很有意思,忍不住和他私聊,并约定一起写生。
我们约在南锣鼓巷见面,他带了个大包,穿着一身很简单的衣服。与我心目中醉情创作的艺术家形象有很大出入。
我们计划在鼓楼写生,炒饼从包里把颜料、墨水、笔盒和本子一件件地拿出来。我好奇地端详他的动作,没想到他最后竟然掏出一把折叠椅。他笑称这是“龙椅”,我说我平时画画都坐在肯德基的垫盘纸上。他二话不说就把“龙椅”让给了我,自己坐在冒着热气的地面上。

地面被太阳晒得滚烫,即使这样,炒饼还是把折叠椅让给了我
炒饼带我逛了南锣鼓巷,我们顺着巷子走到后海。8月末的北京已经不太热了,水面上的风拂在身上很凉爽。炒饼在路边买了两瓶酸奶请我喝,也打开了话匣子,走累了就带我躲到树荫下休息。

后海的景色十分美丽,河岸对面有一座矮矮的塔形建筑,远处的水面在太阳的照耀下波光粼粼,近处是被风微微吹拂的柳条,炒饼看我入神的样子,问:“想不想画一下?”
我正有此意,于是我俩坐在石沿上开始画画。往来的游客很多,有的好奇地静静观摩一会儿,还有大爷走过来问我俩是不是美院出来写生的学生,还没等我们答话,大爷就又径自说起来:“美院我熟啊,是央美还是国美?看你俩画的画,是国画吧?哎哟,小姑娘画的颜色真棒,小伙子就不行了,画得有点慢啊,要继续努力了!”大爷走后我才敢大笑,炒饼说北京的大爷就是这样,习惯了就好了。
两个人这样坐在路边很容易被人围观,有时是大爷大妈,有时是小孩子,年轻人几乎不怎么出声,看一眼就走了,特别感兴趣的会静静地站在我们旁边看一会儿,等我们画完才过来搭话。

炒饼画画时很投入,他画得极慢,好像怕画快了钢笔出水的速度就跟不上一样。
有好友看了我跟炒饼画画以后说,我画画就是画画,炒饼画画是绣花,虽然有点好笑,但这个形容确实很贴切。我早已画完到处溜达,炒饼还在细致地雕琢细节,完全没注意到太阳就要落山了。
和我粗犷的写意画风不同,炒饼的画像是在复刻场景。被我在社交软件上点了很多次赞的小区门口的大树,就是炒饼一片叶子一片叶子地细致描绘出来的,因为一天画不完,他就端着板凳带着猫画了3天。得知此事,我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我从来没在外出写生时花费超过3小时的时间,原来写生是可以画这么久的吗?!
一个人的性格可以通过他画的画表现出来,炒饼心思很细腻,他的画也很细致,他的画长线条板正到好像是用尺子比着画出来的。我的性格和炒饼完全相反,大大咧咧,做事不拘小节,很害怕麻烦,画画时线条也比较粗,遇到难画的部分就用圈圈草草地带过了。


大学时我就开始观察自己的性格,但即使是有意识地反思自己,我也很容易忽略很多细节。人就像一面镜子,可以反映万物,却唯独照不到自己。
我对性格的思考一直没有停止过,有段时间我读了《鬼谷子》,这本书认为人不应该说很多话,一个有权谋的人要少说话,一来言多必失,二来自己少说话对方就会多说话,大部分人喜欢倾诉而不是倾听。读完之后我仿佛醍醐灌顶,有意控制发言次数,但后来我发现我做不到“噤若寒蝉”,因为我本身是很外向、很喜欢分享的人,有想说的话就会说出来,为此我颇懊恼了一番。大学邻班一个同学说话做事都比较谨慎,非必要不发言,我十分敬佩她,但与她相处久了发现,内向型的性格并不是完美的:内向往往伴随着敏感,大量的猜测和内耗会随之而来;因为寡言少语,也很难让周围的人真正理解自己。
每个性格类型都像磁铁一样,会排斥一些人,也会吸引一些人,这很正常,如果强行改变自己,排斥人的力量会减弱,但吸引人的力量也会减弱,没有所谓的“好性格”和“坏性格”之分,做自己就好。
第二天,炒饼带我逛前门大街。他说昨晚熬夜把白天画的线稿上完了色。我走了一天回到酒店倒头便睡,炒饼居然还有精力熬夜画画,我很敬佩他对画画的热情。
炒饼说他今天换了本新奇的本子,还顺手拿出一本带着塑封的本子递给我。这是一本用手工印度纸装订的水彩画本,纸边有手裁留下的毛边,纸张很厚但手感较软,纸纹明显,用钢笔在其上作画会稍微氤墨,形成一种独特的肌理感。这种画本当时国内只有一两家淘宝店在卖,想买还要预购,等店主从印度发货。炒饼解释他前段时间就找代购买了一大一小两本画本,我突然来也没什么礼物送我,昨天看我拿着小开本画画,就想送我这本尺寸相近的小号本子,我惊喜地谢过他。

上午天气实在太热了,炒饼带我到前门大街的书店里避暑,像昨天一样,我们边逛边找画画对象。二楼的电梯旁有一扇落地窗,从这里刚好可以看到完整的前门门楼,炒饼看我有点儿心动,说要不就画这里吧。我在心里感激他的体贴。
正当我们两个要席地而坐的时候,店里的保安过来驱赶,暗示我俩这样有损书店形象。我们灰溜溜地收拾好画具后在店里徘徊,不甘心就这么两手空空地打道回府。炒饼突然发现消费区玻璃窗外的一座建筑很好看,我们商量几分钟后决定斥“巨资”买一杯30元的浓缩咖啡坐下。

这座红色的建筑是盐业银行旧址,我在百度地图上搜了好长时间都没搜到,最后还是问了几个店员才知道它的名字,我和炒饼感觉挖到了宝藏。这家银行是1915年创办的,当时名声响亮。
我经常在旅行中看到一些老建筑,但除了路过时在心里默念一声真好看外再没做过其他事。可能像我一样走马观花的人太多了,这些原本在当时煊赫一时的建筑一旦失去使用价值就会慢慢被人遗忘。
我们怎么向世界证明“存在”呢?靠物体的客观物质性吗?那留存在人类意识之外、尚未被人观察到的客观存在能被说成“存在”吗?即使被人观察到,但无人在意的“存在”还算是“存在”吗?翻起手绘本时我有点儿庆幸,如果有一天这座建筑被拆除后盖了新楼,或许大多数人都不会知道它是盐业银行旧址,但我知道;如果这座建筑能长久挺立在前门,那世界上就多了一个走过但没有忽略它的存在的人,它存在的确定性就多了一分。
城市速写是西雅图记者兼设计师Gabriel Campanario在2007年创建的速写组织,其宗旨是以速写的方式绘画自己所居住的城市。目前城市速写在中国还处于初期发展阶段,具有成熟组织形式的国内速写群体有速写北京、速写南京、速写东莞、速写乌鲁木齐、速写长沙等。若读者想要加入当地速写的组织,可以在微信搜索栏搜索“速写”+“城市名”,大多数速写组织都有微信公众号,按指引加入群聊就可以参加活动了,而且这些活动都是免费的。除了速写外,有的地方的速写组织还会举行画画沙龙、分享会、年会、聚餐等活动。
在北京的最后一天,我和炒饼参加了速写北京(Urban Sketchers Beijing)的周末速写活动,成员们约定在北大红楼写生。
我虽然之前就在社交平台上看过城市速写官方账号发的成员作品,但真正参加活动这还是第一次。炒饼向其他成员打招呼并热情地介绍我,速写北京的成员结构很丰富,从八九岁的孩子到60多岁的老人,从设计师、编辑到研究员,各行各业的人都有。已经有人开始画画了,炒饼先带我参观了北大红楼内部,然后招呼我坐下和大家一起画。


活动结束时大家的作品被放在一起展示,虽然这次活动的主题是北大红楼,但大家画的内容很丰富,除了画建筑的,还有画花草的、画速写者们的,来晚了的成员虽然只画了几笔,但也大大方方地将作品展示了出来。
此外,大家画的北大红楼也不尽相同,有的楼旁边有小草,有的没有;有的楼的颜色是偏橙色的,而有的楼的颜色是偏紫色的。
人眼所及的范围内,事物细节非常多,而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经常注意到这个,忽视了那个。平时我们若没有和别人进行客观对比的习惯,就很容易忽略这一点。大家在日后如果能把自己的所见都如实地描画出来,就能清晰地发现每个人在观察事物时的角度各不相同。看到表现非常翔实的北大红楼速写时我会很感动,因为通常只有用心观察且生活经验丰富的人才能看到如此多的细节。
北京之旅结束后的好几个月我一直忙着准备毕业论文,再一次和炒饼见面是在秋天,我撺掇炒饼来山西做客。我们详细地制订了旅行计划,从大同开始一路向南,边走边画,探索山西的古建。

我们约定在大同会合,因为我要等辅导员批准了才能出校,所以炒饼比我先到,等我到大同的时候就享受到了炒饼的接机服务。在出租车上炒饼掏出一副无指手套递给我,说:“看了天气预报提前准备了两副手套,你一副我一副,戴着这个画画手就不冷了。”我感激地直呼他真贴心。
白天我们先去了大同旧城区写生,到了才发现市民基本都到新城区居住了,旧城区几近荒废。和我们想象中的“旧屋”不同,无人居住的房子被主人用来饲养牲畜,没有我们期望的被时光侵蚀而呈现出来的老旧感,只有厚厚的灰尘和蜘蛛网。
我们在巷子里钻来钻去,终于找到一个废弃凋敝但别有味道的院子,于是决定就画这个院子。大同的气温比太原低很多,坐在背阴里3个小时,脚早已经被冻麻了,我冷得受不了,掏出暖宝宝贴在鞋垫上,第一次用没经验,暖宝宝没接触空气根本不发热,我又把身子挪到阳光下面。炒饼虽然被冻得嘴唇发白,但还在认真地画,我劝他到阳光下暖暖身子,他说动了位置透视就不一样了,还是坐那儿吧。
下午我们去了云冈石窟,因为没有提前做功课,看着一尊尊大佛除了感叹“真高”“真美”“真厉害”以外说不出别的。我虽然去过很多地方,但脑袋空空,每天只玩不想,除了吃喝玩乐再没有更深的体会。
对事物的洞察是基于个人的深入了解和思考的,这种能力需要有意识地培养和阅历的积淀。我曾无数次后悔自己少时的肤浅,但老话说得好,人走过的每一步都算数,没有幼稚哪来成熟?珍惜现在吧。

我和炒饼坐在佛窟外的长凳上画画,被冻过后有了经验,我在薄袜子外又套了两层厚袜子,虽然挤脚了些但非常暖和。人往往是解决了“温饱”问题才能更重视精神提升,我在云冈石窟画画的专注度比在旧城区高了很多,炒饼都夸我超常发挥。
冬日的下午一转眼就过去了,但时候尚早,我们一起去看电影。电影是当季正热的《找到你》,电影讲的是一位离异女律师,为了抚养女儿拼尽全力工作,孩子的生活交由保姆照顾。但有一天,保姆带着孩子消失,女律师如遭五雷轰顶,由此发生一系列惊心动魄的追孩故事。结局虽然圆满,但从电影中反映出来的当代女性困境让我感觉很压抑。
我沉默着从黑压压的影厅出来,我们立刻互相分享观影体会,他的体会和我截然不同。我很诧异,他居然和我有如此大的分歧,气愤地和他辩论。
这样的气愤我很熟悉。以前我沉迷于综艺节目《圆桌派》,其中一期请某心理学教授做客,教授对于年轻人一针见血的评论让我马上成了她的粉丝,我开始专门找教授的视频来看,看得不过瘾又去微博关注她。
这一关注麻烦就来了,我发现她的微博里写了好多“父母与孩子的4种缘”“做人要像唐僧”等在当时的我看来是“反智”的内容,我觉得微博上的她完全不像节目里睿智的女教授。我把这种失望分享给朋友,他反应却很平淡,说:“人不是扁平的,不要‘神化’人,要避免产生对完美人格的期望。”
朋友的话让当时的我瞬间清醒,炒饼不也一样吗,观点不同只能说明在这件事上他与我的看法不一,并不能说明他是坏人,上升到价值观更是小题大做。不要说人与人对于某一件事的看法不同,去年的我的想法和今年的我的想法都有很大出入,接受不了不一样的声音未免有点狭隘了。想到这儿我有点羞愧,虽然没有直接道歉,但我主动付了回酒店的车费,希望炒饼能从这一举动中读懂我微妙的情绪变化和歉意。
下一站我们决定坐火车去太原。炒饼本来想看应县木塔,当时我并不理解一座塔有什么好看的,炒饼跟我解释说应县木塔是现存最古老也是最高的木结构佛塔,梁思成当年还亲自去考察过,就是因为他,这座塔后来才与比萨斜塔、埃菲尔铁塔并称“世界三大奇塔”。我没听炒饼的话,连哄带骗劝他。炒饼耳根子软,没多久就买了去太原的火车票。两年后我到炒饼家做客,在他的书柜里发现了一本《梁思成纪念文集》,书中用很大的篇幅记录了应县木塔和中国建筑的渊源,那时我才明白没去看应县木塔应该是炒饼的遗憾吧。

在火车上我们也没闲着,拿出本子就开始画。我画坐在我们对面的两个小女孩,炒饼画我。炒饼好像不太擅长画人物,把我画得巨丑还不让看,最后实在画不下去了,他合起本子讪讪地给我端颜料。其实我才是最不擅长画人物的,炒饼有扎实的美术功底,人物速写比我画得好很多。可能就是因为没有受过正经的美术训练,我对自己的创作没有明确的好坏判断,高兴时就画,画坏了虽然气恼但也不怎么在意,我更关注画画时的情感体验,那种一沉进去就无视时间和空间变化的投入感。心理学上用“心流”一词概括这种投入感,我喜欢画画时的心流。

炒饼和我在街上画速写
到太原后炒饼突然有事提前离开,剩下的旅程我不想放弃,于是用快近周的时间走完了。我抱怨过炒饼的失信,但又感于万事不能强求。朋友就是,你走这条路,我恰好也走这条路,两人可以互相陪伴着前行,中途任何一方要退出,另一方也得摆正心态接受。友谊绝不是靠生拉硬拽、拼死挽留就能得到的,我很快也就释怀了。

炒饼离开后,我按计划走完了剩下的旅程 晋祠

常家庄园

飞虹琉璃宝塔
元旦炒饼叫我去广州跨年,那应该是我们最后一次相伴出行。玩了什么,画了什么,我都不太记得了,只记得最后一天在白云机场等凌晨的航班时,为了克服睡意我拿出画笔画画,半睡半醒的炒饼成了我的模特。迷糊中我问炒饼为什么叫炒饼,他说他大学时老吃炒饼,同学就叫他炒饼,这个名字就用到了现在。
和炒饼一起画画是我旅行中非常快乐的时光之一,我们节奏一致,不用规划路线、不用赶时间,看到好玩的两人一合计就赶紧拿笔画下来,就算被人围观也不会感到窘迫,反正旁边有人陪着。虽然避免不了人与人相处必定会暴露的缺点,但我们学着互相包容和体谅。就像朋友说的,不要“神化”人,拥抱现实和真诚。


炒饼每走完一个城市就把他画的画印成明信片寄给我的,有一次他发现精心准备火漆被我撕烂了之后,当时时没说什么,但再寄明信片时就附上了“温馨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