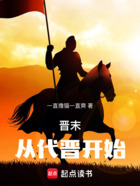
第20章 应对之策,比死难受
桓玄也是神情莫名,对何澹之的立场,产生了怀疑。
一时间,府堂内气氛很诡谲。
何澹之轻笑一声,朗声道:“冯将军误会,还请听何某娓娓道来。”
“哼!今日你若不能说出个一二三,本将军便教你好看!”冯该话语中充满威胁。
何澹之怡然不惧,胸有成竹道:“冯将军且听好了。”
“司马元显已察觉谢琰异常,却依然支持建立南府军,可见他已然深思熟虑。”
“此事各士族,甚至皇室必定竭力劝阻,司马元显面临的压力空前巨大,尚有可能改弦更张。”
“然而,南府军建立初衷,是为防范主上。您若竭力上疏阻止,必然适得其反,令司马元显断定您心中忧惧,反而会坚定建立南府军!”
经过何澹之这一分析,桓玄看向他的目光,也变得欣赏起来。
据传闻,此人为王恭参军时,识破刘牢之反叛之心,前去王恭府上劝告。
可王恭因其与刘牢之有嫌隙,不信劝言,命护卫直接将他架出州府。
这何澹之绝望之余,在府门外哭得声嘶力竭。
倒也算得上忠良之人。
冯该众将略微思索后,神情也缓和下来。
甚至,冯该还主动拱手一揖,歉意道:“还请何参军见谅,是我等思虑不周。”
何澹之并非不识好歹之人,连忙还礼,嘴上谦虚:“冯将军言重。诸位将军只是乍闻此事,关心则乱而已。”
府堂内,瞬间一派融洽。
与冯该等人客套完后,处于高光时刻的何澹之,余光扫向卞范之,却有些惊疑。
被自己抢了风头,居然还能如此淡然?
桓玄想继续听听卞范之的话,看他是否有更中肯建议:“范之,你有何高见?”
安静坐于堂下的卞范之,闻言淡淡一笑:“回禀主上,高见谈不上,仅些许建议罢了。”
“立南府军,确为元显钳制手段。然,谢琰募集三吴流民,以充兵役,与北府、西府士卒相比,素质、胆气先天不足,暂时不足为虑。”
“主上大敌,依旧是北府军。而刘牢之自恃勇武,拥兵自重,与元显素有不合,彼此忌惮。观其劣迹秉性,乃反复小人。主上何不遣人试探于他,与之虚以逶迤一番?”
“若与刘牢之达成盟誓,主上便可兵下建康。即使不成,也能在其脑后再种反骨,只需关键时刻诱导,便能将他策反!”
桓玄眼睛一亮。
这正是他想要的破局对策。
“此计甚妙!甚妙!”
“范之大才也,就依你之见,立即命桓石生秘密游说!”
京师几名桓氏子弟中,桓石生一直在向荆州传递密信,乃是桓玄在京师的眼线。
其余将士亦是赞不绝口,此计策比何澹之的要好不少。
两人策略,各有长处。
一个是无为而治,避免打草惊蛇,
一个是主动谋划,抓住性格弱点。
“是,主上。”时刻关注桓玄的万盖,第一时间应下。
先前没留神,接密信时被丁仙期抢了先,现在肯定不能再落下。
桓玄随后又道:“当然,何参军所谏,亦是良言,本郡公也会采纳。”
“吾,便静观其变。”
忧心之事有了对策,桓玄心情畅快,命人为在座属官、将领添上酒水。
“今日得诸位秒计,暂了一桩心事,我与诸君,不醉不归!”
...
京师这边。
在王谧上蹿下跳游说下,经过两三日发酵后,一众权贵、士族纷纷登门西府,或诚恳,或声泪俱下进谏。
可司马元显已是铁了心,要促成南府军建立,直接命人将他们赶走。
这些人只能转头跑去找司马道子,求老相国出山,劝阻世子司马元显。
司马道子被扰得不厌其烦,只能一摇三晃,找上门。
“父王今日前来,可是有要事?”
司马元显将他迎进府中,亲自扶他坐下。
微醺的司马道子,大着舌头道:“要事?本王哪敢有要事。”
这夹枪带棒的话,令司马元显脸色一变。
他今日姿态放得极低,自认为态度已经非常和善,未曾想父王毫不领情。
司马元显挥退左右侍从、护卫,稳稳坐到司马道子面前,声音低沉道:“父王,儿臣并未觉得自己有何过错。”
他明白父王来的目的,也知道其心中有怨言,但他并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
司马道子半眯着眼,毫不客气质问:“你暗中夺本王大权,现在又要动摇国本,还不觉得自己有错?”
见司马道子终于吐露心声,司马元显也打开天窗说亮话。
“父王,当初王恭连续两次叛乱,您已在朝中威信扫地,我皇室皇权本就孱弱,若由您继续带领,将更加被人看低。”
“儿臣冒大不韪,趁您酒醉攥权,于礼制虽有逾越,可实际是为我晋室着想,还请父王理解。”
这话,自前年夺权,父子关系陷入僵局后,司马元显就想找机会说出口了。
只是司马道子一直在生他的气,且无日不醉,便一直拖着。
好在今日总算一吐为快。
司马道子闻言沉默下来。
他有自知之明,清楚儿子并非胡言。
当初,自己因母后李陵容的宠溺,才能与皇兄司马曜争权,展开所谓的“帝相之争”。
及至皇兄骤崩,贵为相国的他更是权倾朝野,声望达到巅峰。
一时风头无两。
但王恭第一次叛乱,就逼得他毫无办法,最后不得不抛弃王国宝、王绪等亲信,苟全性命。
可谓是颜面扫地,多年树立的威信,也荡然无存。
他丢了人,间接的,也相当于整个司马皇室,被王恭狠狠扇了一嘴巴子。
朝臣们不敢继续依附于他。
毕竟连亲信都保不住,谁还敢给他卖命,都要担心哪天被扔出去,做了替罪羊。
王恭第二次叛乱也大同小异。
自己惧怕不已,将大小事务都扔给司马元显后,躲到府中整日酗酒,不理政务。
可以说毫无担当。
若非司马元显临时策反刘牢之,两父子说不定坟头草都三米高了...
想到这里,司马道子面有愧色。
司马元显见状,也没继续揪着不放:“至于动摇国本,儿臣认为此乃谬论。”
对被夺权的事,司马道子还算自觉理亏,属于德不配位。
但设立新军府,他就敢理直气壮训斥。
只见他眉毛一竖,出言讥讽:“谬论?朝中皆传,你枉顾安定大势,暗藏野心,欲立新军府,挑起天下纷争!”
司马元显挑了挑眉,似笑非笑反问:“谁在传?”
司马道子当然不可能实话实说,恼怒道:“你自己心知肚明!”
司马元显一一点名:“我猜猜,太原王氏?”
“不太可能,王国宝之后,他们就一蹶不振,一直想巴结于我。”
“庾氏、桓氏更不可能。”
“那就只剩琅琊王氏的人。是了,王谢两家的腌臜事,众所周知。”
近日,他忙着与张法顺等人商议新军府的事,确实没精力去调查,谁在背后搅风搅雨。
对诏令被司马德文暗中使人压下的事,这他倒是知道。
除却有些惊诧,对这个傀儡司徒升起一丝警惕外,其他没多大感觉。
只当是发现了个乐子。
闻言,司马道子偏过头,不想理睬他。
司马元显微微一笑,哪还不知道自己猜中了主谋。
不过南府军这事,各个士族肯定是反对的。
不然也不会一被游说,就成群结队跳出来。
想到这些士族的德性,司马元显劝解道:“士族高门压制我皇室百余年,父王应与这些朝臣保持距离,少听他们的离间谗言,要相信儿臣。”
司马道子顿时勃然大怒:“怎么,你还想幽禁本王?”
“去年吏部尚书车胤见你骄纵,表请我加以制约,事后不久,车胤便自杀,是不是你所为?!”
这事在他心中,一直如鲠在喉。
车胤幼年囊萤夜读,得举入朝为官,任劳任怨;中年刚正不阿,兼任国子博士,桃李满天下;临到晚年,却被活活逼死。
司马道子不甚惋惜。
这般尽心竭力,又声望极高的臣子,大晋太缺了。
司马元显眼神有些躲闪,这事确实是他干的。
不过他也没想到,只是让人上门去训斥一番,那姓车的居然直接吓得自杀了。
这脆弱心态,也不知是怎么当上三品重臣的。
见司马元显这副模样,司马道子已经气得不想说话了,许久之后,才长叹一声:“哎…吾儿,收手吧,南府军兹事体大,牵一发动全身。”
司马元显还以为车胤的事,自己要被训斥一番,未曾想居然就这样揭过了。
也对,人都死了,再说有什么用?
不过对立军府之事,他肯定不会松口:“父王,您应该理解儿臣,此举并非动摇国本,相反,还利于巩固我晋室江山。”
司马道子当即就要驳斥,被他伸手拦住:“父王且听我把话说完。”
“桓玄窥视我大晋,已几次想借征讨孙恩之名发兵,给京师的压力太大。北府军刘牢之,也一直游离于我的掌控之外,为不安定因素。”
“我大晋两只强军,居然都不在皇室手中,简直可笑至极。”
这话令司马道子酒醒了一半,只因司马元显所说都是事实。
“因此,我才顺势而为,应承谢氏请求,在三吴之地组建南府军,作为我晋室独掌军队。”
“对谢琰的异常,不过我已在妥善布置,定能从其手中夺下兵权。”
司马元显言辞中,充满强大自信。
司马道子也彻底酒醒。
心中对皇室掌控军队这点,很认同。
此前,他担心的是谢琰独立成军,成为刘牢之、桓玄一样的藩镇军阀。
那晋室就真的无力回天了。
不过,想到当年他是与皇兄一起联手,才逼得谢安、谢玄退位让贤,而今司马元显却只有一人。
不免有些担忧。
可司马道子随即又自嘲一笑。
自己在这里杞人忧天个什么劲,这逆子夺他权柄,断然不可能让他重新掌权。
忽然间就有些心灰意冷。
然后,在司马元显诧异目光中,司马道子踉跄着站起身来,一步步走向府外...
...
京师乃至荆州的谋划,远在三吴的谢琰、谢混毫不知情。
谢琰率军回到会稽后,继续有条不紊的募兵、练兵,施仁政。
谢混领着蒯恩他们,镇守句章。
自那日檀氏三兄弟用过铁铳,反应也如蒯恩两人一样,回来见到谢混,就立即跪下,宣誓生死相随。
而后更是一封书信,将檀凭之从京师招过来,做了谢琰的参军。
郡府中。
谢混与刘穆之喝着茶,相对而坐。
“穆之,此次追击贼寇阵亡将士,统计的如何?”
孙恩被赶回海上,已是元气大伤,短时间不敢继续来犯。
谢混便开始考虑收买军心。
“回主上,您从句章带过去的士卒,阵亡五百余人,伤残一千余人。”刘穆之声音有些低沉。
阵亡的士卒不用说,已经客死他乡。
七月天气炎热,为防止瘟疫,尸体都已就地掩埋。
伤残的一千人,小伤还好,能医治。
大病、残疾的,则有些可怜了。
农事、兵事,都不能参与。
这辈子算废了,活着比死了还难受。
“阵亡的士卒,按常规,其名镌刻在石碑上,再每人发放两百铢钱,必须送至直系亲属手中,并给予土地、米谷等补偿。”
“此事你严厉监督,若是被我发现有人中饱私囊,拿你是问!”
谢混说到最后,声色俱厉。
喝兵血,截留抚恤金,克扣饷钱和军粮,倒卖马匹与武器,每个朝代都存在。
他暂时管不了那么多,也管不了那么宽。
但在这句章城,他是郡太守,就得按他的规矩办事!
“是,主上!”
刘穆之神情严肃,同样厌恶这种行径。
随后他补充道:“此前在吴郡城,有人于城下发现了太守袁崧的尸体,疑似跳城楼殉国。”
“海盐令之子鲍嗣之也死于城外,倒是广武将军桓宝,幸存下来。”
谢混有些沉默,袁崧殉国,这是他没想到的。
他还评论过此人,定是贪生怕死之辈,未曾想,墙头草也有忠义之人。
至于桓宝和鲍嗣之,都是在城外被发现。
这事想都不用想,二人必定是在城破之时,做了逃兵,破围而出。
对这三人,谢混逐一安排:“袁崧尸体送回家中,并请我父亲为其向朝廷要追封。鲍嗣之送还海盐令鲍陋即可。至于桓宝,密信我父亲,把他遣反回朝中。”
袁崧可以被礼遇尊重,鲍嗣之纯粹就是自己找死,能将他送还鲍陋,已算是仁至义尽。
桓宝勇猛有余,却自私自利,临阵脱逃,他不需要这样的将领。
况且,桓宝出自桓氏,送离三吴最恰当。
随后,谢混招呼刘穆之:“走,随我去看看伤残士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