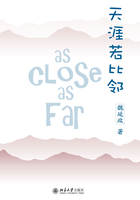
天涯若比邻
2013年3月27日
这段时间,通过QQ、微信联系上许多过去中小学的同学和朋友。今天加了一个同学,她的名字让我想起大学的一个同学。于是发了条腾讯说说,引来一些讨论,因此有了点想把这些有关童年友谊的记忆记录下来的冲动,分享给朋友们。本想题目叫做“友谊”,但未免落入俗套,体现不出我们时间、空间都隔了这么久远还能常常联系,所以“天涯若比邻”这个题目最贴切。想到七年前就以此为题写了有关大学同学的文章,这篇就算是姊妹篇吧。
我大学有个中文系的同学叫张惠文,总觉得她和我小学六年级的同桌张惠武有点关系,一个会文一个会武。还有台湾那个唱歌的,既不会文又不会武,就会唱歌,为了在两岸四地多拉些“粉丝”票友,所以她家老三的名字走了大众化路线,以妹妹相称,叫张惠妹。她家老三失散在台湾多年,常常以歌声诉说怀乡之情,整日“站在高岗上”,望眼欲穿海峡这边的俩“姊妹”,期望“牵手”。此情可待会有时,等海峡两岸统一了,惠文、惠武、惠妹这三姐妹就可以聚首了。
上面这条说说发出不久,马艳就看到了,说要转给张惠武看看。并且说她们三姐妹那还需要我的牵线才能聚首,相约我们要等到那一天。我知道马艳是在鼓励我面对病魔要坚持,感动在心、鼓舞在手,速回复:一定!她家老三要是再敢给哪个欠扁的唱国歌,老兄我立刻提刀上马杀将过去,把她家老三立时掳过来见她家兄长姐长谢罪请安问好。马艳又说:她家老三胖得已经没法看了,估计没人请她唱了,嘻嘻,老二惠武还苗条得不得了呢。我告诉“马宫主”一件陈年往事:她家老二和我同桌那年参加省电视台的合唱团,唱歌那嗓音,美!每次她在班里唱歌,以距离计算,我都是第一个听见,虽然她的声音传到我的耳朵里比传到其他人那也就早那么0.01秒,但每次我都认为她是先唱给我听的,哈哈。马艳方知原来还有这档子事,惠武小学就有我这么个“粉丝”。
其实,大家都是平凡的人,虽平凡,但各有特色。我相信每个人都有“粉丝”,甚至是铁杆“粉丝”或暗恋过自己的知己,只是自己过了许多年或者几十年都不曾知道。有一次我和于炜聊天,我说他有好些“粉丝”,他也不相信。他说,要是中学的时候就告诉他这回事,那……对呀,假如那时我就告诉于炜有若干漂亮妹妹是他的“粉丝”,那他会怎么样呢?我想答案是——那就太好了!朋友,你不会对我的这个答案感到失望吧?如果你和我同龄或者比我年长,就应该不会。因为时光无法倒流,一切也不会因为一个假如而有任何改变。我们只好对自己说,那就太好了!那真是太美好了——童年的友谊!写到这里我的眼中有些潮润。
马艳说,于炜讲相声的时候,给我们带来了不少欢乐。我们那个学校,用一个当年四川来的转校生的话说,是藏龙卧虎。于炜就是这样的龙虎人才之一。每年元旦时的新年晚会,甭管几万人的大企业有多少文艺大腕,能容纳几千人的大礼堂的这场晚会的压轴大戏一定是于炜的相声。如果说,我们的童年是听着孙敬修老爷爷的《西游记》故事在幼儿园里度过的,那么可以不夸张地说,我们的中小学时代是在每年一度的新年钟声敲响之际听着于炜同学的相声度过的。
当初我们那个小学校,虽也是子弟学校,却比不得财大气粗的邻居——铁路中学,人家那里软件、硬件都是上乘的;当初我们那个穷学校,走出来的学生一看衣着,就知道是铁路子弟学校的而不是四建子弟学校的;当初我们那个破学校,虽破烂不堪,在乌鲁木齐百所中学中名列倒数,但我们对她的感情依旧深厚,用一句俗语形容很贴切——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就像是老婆,只能自己数落她的不好,但凡有别人说自己老婆不好,立刻扁他!
我和于炜的渊源是从幼儿园穿开裆裤时就开始的。从幼儿园直到小学毕业,我都属于比较内向的,没怎么和于炜说过话。中学自习课时常听于炜坐在我背后唱歌。那时我还没有在笔记本上抄歌词的习惯,所以对很多流行歌的歌词不是很清楚。有时听到于炜唱到某处,我会根据歌词的谐音展开联想,偶尔还会闷骚地插句嘴。有次班主任陈凤英老师正在挨个检查同学们背诵英语课文,由于距离还算比较远,于炜便偷着唱姜育恒的《跟往事干杯》。他的声音比较小,我听不清,就问他:“跟老师干杯”?于炜乐了,“哼哼哼,你说跟老鹰干杯?你要有胆还是你去吧,我很想看看你说,‘老鹰,来干一杯’,看她是啥反应”。我们都乐了。
大一那年“五一”,于炜和肉肉从天津来北京找我玩。我找了宿舍里功率最大的录音机把《梦回唐朝》放到音量最大,欢迎他俩的到来。童年的情谊随着喧嚣的摇滚,陪伴我们走到很“二”的年纪。今年春节我问于炜,还敢像当年那样一起高放唐朝乐队的歌吗?于炜淡定地一笑,哼哼,那时候“二”叫做“个性”;现在“二”叫做“勇气”。
那年暑假,胡月没有提前预订回新疆的火车票,于是我和于炜在人大旁边的小售票亭帮她排了一通宵的长队,冒着通宵的倾盆大雨,露宿在和胡月温暖的女生宿舍楼仅有一墙之隔的中关村北大街,那时还叫白颐路。要知道北京7月的大雨可以让北京西客站的楼顶坍塌,也可以把蔡国庆的歌里千姿百态的“北京的桥”通通变成东方威尼斯的海底隧道。无处藏身,旱鸭落水,我和于炜喝着二锅头,唱着臧天朔的《朋友》,惦记着胡月温暖的被窝,好给心里增添一丝暖意。第二天,我俩把火车票送到胡月手里,用积攒了一通宵又半天的空腹把北大西南门口的包子铺里剩下的几笼包子一口气吃了个精光。记得有两个稍微晚来两分钟也要买包子的人,我俩凶悍地说:“我们先来的,这里的包子我们全包了,你俩别处吃去!”看着于炜高大的身形,包子铺老板毫不怀疑他的食量,但对于我和于炜同样的装载速度和装载数量,包子铺老板惶恐不安。我暗自发誓,以后谁要是瞧不起我的实力,我就让他先领教我的“食力”!




2014年8月12日,见到了1988—1991年我们的初中班主任陈凤英老师,也就是这篇文章中我们敬爱的“老鹰”老师。二十多年后她依然精神矍铄、神采奕奕。
要说于炜有多少“粉丝”,可不要太多,分三个梯队还得加个特级档,其中必不乏大眼、高鼻、长腿、翘臀的红粉靓妹。但是,不知道于炜心目中是否有他所朝思暮想、夜不能寐的“那个她”,如果有的话,在如此众多的“粉丝妹”中脱颖而出,也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二十多年之后,我告诉他曾有不少靓妹关注过他,我俩都唏嘘不已。用三首赵传的歌来形容他这二十多年来的心路历程最恰当不过:《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请你为我再将双手舞动》《我终于失去了你》!
当年没敢鼓足勇气向于炜表白的“粉丝”们,看到这里,你们是不是想起赵传另外一首充满幽怨的歌——《我一直以为你知道》……如果想到这首歌的是位男“粉丝”,如今,你也不必为有这种想法而难为情,只是,这个想法还是永远保留在心里,就“一直以为他知道”了吧。
我们大家对童年的青涩回忆,不免都有些许怅惘,那时都不开窍,但都是最真挚的友谊。刚才用赵传的几首歌小小打了个趣。其实,我的同龄朋友们,我想,你们和我对童年往事、友情的回忆,应该恰如赵传这几首歌所流露的真实情感——深沉、有力——把放不下的情感,“再勇敢一点”扛起来!这才是赵传歌声穿透我们心灵的真谛。
那篇不足140字的腾讯说说引来这么一通浮想。终于,张惠武看到了我的这条说说。我问她,还记得我们什么时候做的同桌吗?她的记性很好,我也记得些许细节。六年级时我和她有大半年是同桌,李建民和胡月是我俩前面的一对同桌,他俩老说话,老师就把两个女生前后对调,所以我又和胡月同桌了小半年。我说,很想穿越回1988年小学六年级时,因为我印象最深的三个小学老师有两个都是那时教我的。
第一个印象深刻的老师是于炜的妈妈回老师,也是小学教我们时间最长的老师。回老师标准的普通话发音,让我们这些父母来自天南海北的孩子,在接受完幼儿园阿姨浓重的河南、山东口音之后,统一了标准的普通话发音。记得当初幼儿园里的一首儿歌是用这样的口音教的——我们也是这样学的——呗凤糊糊锤亚(北风呼呼吹呀),动舔来到聊(冬天来到了),呗扇上滴淆套树呀谮墨受得聊(北山上的葡萄树呀怎么受得了),泥去拿马绳亚(你去拿马绳呀),喔去抱到曹(我去抱稻草),给咱们家滴淆套树呀传个大面敖(给咱们家的葡萄树呀穿个大棉袄)。虽然后来大家都学了一点新疆本地口音,以防不时之需,但标准的普通话一直伴随着我到现在。记得1998年春节在新疆乘车,用普通话问票价,答曰:“5块!”我随即改用新疆口音嘀咕了一句:“咋涨得这么快?”答曰:“2块!”
还有两位印象深刻的小学老师,一位是平琳的妈妈郭老师,教大家数学,从五年级教到六年级。也就是在六年级那年,我参加乌鲁木齐小学数学竞赛拿到前几名的好名次,后来高三时还参加了全国数学联赛,也拿了奖,应该说,这些成绩和好运都是从郭老师教我数学起开始的。另外一位老师,是我们当时6班同学都深深敬仰的语文老师陶老师。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被当时胡月一篇作文里的一个故事深深打动了:那时的班主任都非常负责,常常陪学生补课到很晚,甚至到自家晚饭不做、不吃的地步。某天晚上,陶老师听说杨同学放学去从事一些危险活动,虽然当时已经很晚了,陶老师还是用胖胖的身体骑着自行车绕四建老远追寻杨同学,直到找到他并把他送回家。
张惠武在微信里问我还记不记得她很爱哭,说是不成熟的表现。我说当然记得,爱不爱哭与成不成熟没有关系,只是泪点低一些;有的人从来不哭,老是笑,笑点老低了,也不代表他成熟嘛。这话把她逗乐了。其实爱哭爱笑的人有个好处,就是什么事都不往心里去,宣泄出来了没压力,反而从里到外一身轻松,所以惠武到现在还像个学生妹一样年轻苗条,不像她家老三,别看演唱会海报上、封面杂志上她露个脸老是笑,那是摄影师不敢往下半身拍——私下里胖得都不成形了,估计也没人请她唱了——马艳也这么说。
1988年是印象深刻的一年,因为从那一年开始逐渐学会观察社会,牛仔裤、霹雳舞、太空步、西北风、费翔,这个世界开始变得多姿多彩。前些天和老婆去卡拉OK,我唱了首费翔的老歌,当年费翔帅气逼人的脸庞映入眼帘的一瞬间,老婆眼睛一亮:“这是谁?那么帅!”是啊,美好的事物和瞬间会成为经典,永恒地存在,即便25年之后,人们的审美标准仍未改变。
写到这里,自己不禁有点诧异,从前的我最讨厌写作文和日记。因为胸腹头脑的空洞。二十多年来,不是因为自己的文笔变好了,而是因为视野随着脚步变宽了,心里装载的事多了,也就有东西可写了。从前,不知道散文是何许事,现在知道了,那就是一种感觉,让它跃然纸上,让读者随之起伏共鸣的感觉。
大家还记得吗?上初中时,老鹰(我就这么称呼她吧,丝毫没有轻蔑的意思,而是对从前老师满满的敬意和亲切;就像前面诉说我在饥寒交迫中惦记着某位女生温暖的被窝一样,没有一丝邪念)让大家每周末写一篇周记。帮大家说句话——当时周记苦煞了所有人,当然也包括我。某日,我奋力一拼,在周记本上一次性把本学期剩下所有周的周记都写完了:把“本周一切正常”这六个字每行一遍写了很多行,也许把下个学期的周记都写完了。老鹰看到我的周记,在班上大声宣布,“魏延政同学就是这样对付我的”,她扬着我的周记本,“你们有啥想法?是不是周记很没意思?要是这样以后大家都不要写了!我也省时间了!”没想到老鹰如此英明,大家高呼万岁。
从前的往事如同费翔的经典造型一般,永恒地留在记忆中。去年读了本李泽厚的书——《美的历程》,里面有很多学院派的理论上的东西。老子说,天地有大美。美就在我们身边,美就在我们眼前。随着年龄的增长、经历的增多,我发现自己正在慢慢地改变。从前,我看待事物往往追求极致完美,公司里参加国际展会凡我出手的材料,必定要止于至善;现在,我往往在不那么完美中去发现它仍存在的美。美的真谛不在于面面俱到,而在于看到它时,我心欢喜。老婆有时念叨这个社会上的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我通过这次生病以来的读书休养,变得开始能容忍那些不如意,开始品尝五味人生的快乐。我不禁喜悦,发自内心地喜悦!
童年的记忆就像飘荡在和煦阳光中的一首首轻柔的乐曲。我相信再过二三十年,对于现在的记忆,同样会是永恒美好的。虽然有些极美的东西无从找寻,就像我对四建子弟学校一次新年晚会上体音美教研组的老师一起合奏的一曲《红楼梦》主题曲的记忆一样,如果有录音,那段演奏必定比不过1987版《红楼梦》原版唱片,但正是因为无从找寻,那段留在记忆中的乐曲却成了我听过的最优美的《红楼梦》主题曲。所以,最美的东西,并不见得是曾经得到或失去的某些具体的事物或成绩,而是我们曾经一起度过的闪亮的青春。
后记:今天这篇文章是由张惠武的名字引起的,还加上了那条说说以及和马艳之间的留言。篇幅有限,没有把所有好友都写进去。但我想,这篇文章里的心情应该是所有同学和好友都能体会并有所共鸣的。

1992年,高一

1993年,高二

1994年,高三

2014 年,20年后再相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