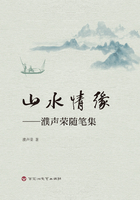
读书
童年的记忆是模糊的。
我究竟何时读书,在童年少年时代读了几年书,我记不清了。
很小时候,母亲带我和维弟在衡阳住过,似乎读过一年小学,不久母亲患病,我就回到了故乡零陵梳子铺。第二年母亲病故,这段时间好像没有上过学。
半年后,父亲与宝雨妈妈结婚,奶奶把我和维弟送到衡阳,这次我和维弟都上了小学。不久,随父亲回到农村梳子铺老家,开始务农,没有再去上学。
当时父亲对我说,我们的祖辈,从高祖父、曾祖父到祖父年轻时代都是种田的。中国是个农业国,种田是根本,不管谁当皇帝,都要农民种田。不管社会多么动乱,只有在乡间种田最为可靠。
父亲读过私塾,也读过官办的中学,初中毕业后,在家中打过两年闲杂,后考取了衡阳邮政局当职员。解放前夕,父亲带我们一家回农村务农。其实,父亲自己并没有干过农活,不会犁田、耙田,割禾插田也不熟练,就是挑担也不行。父亲在衡阳邮局工作,母亲在时,省吃俭用还买了两亩田,加上祖母分给我们的一亩多田,以后土改我们又分得了两亩多田,总共有五六亩水田,近一亩旱地,种好后吃饭还是够的。
我从衡阳回来时,还不满11岁。平常干的农活较杂,什么活都干,但主要是砍柴、锄地、创草皮,放牛、插田、割禾。大概到了12岁,我就学会犁田、耙田了。因为父亲不会干农活,我当时又年小,许多重活、力气活和技术活主要靠外公来做,有时舅父舅娘也来帮忙。
但是在我的记忆里,几乎每年种的粮食都不够吃。每年过年后,粮食就紧张了,特别是五黄六月,春天农活大忙季节,经常吃不饱。冬天常搭一些红薯吃,红薯吃多了,常吐酸水。麦子割了以后,把它磨成粉做粑粑吃。在我们家乡,小麦叫杂粮,不习惯吃,也不会像北方那样吃的花样多,吃米饭才算正餐。
农活永远是做不完,似乎天天都有事做。冬天,田间事少的时候,就去山岭上砍柴。家里做饭烧水炒菜都烧茅柴,即矮小灌木和茅草。当年植被破坏严重,较近的丘陵低山的柴草往往被砍尽,我们就去大岭上,即五岭山脉的越域岭上砍柴,有时还要翻过山岭,到另一面山坡上才能砍到柴,高差两三百米,路途一二十里。一般吃了早饭去,吃下午饭才能回来。砍完柴往回挑的时候,感觉担子越来越重,肚子越来越饿。别人家里往往有兄弟姐妹去岭脚边,去接一下担子,而我呢?弟妹们还小,只能咬着牙,含着眼泪一步一步往家挑,有时天黑了才到家,辛苦劳累可想而知。
直到1952年秋,在外公外婆和奶奶的干预下,我终于去排龙山小学上学了,插班六年一级,当年已14岁。
小学生活是快乐的,吃住都在学校,假日和星期天回家干点农活。家中农活基本都由外公包了。学习非常轻松,此前我读过两年多小学,未读书的日子里,我还常看一些故事类的书。我的记忆力相当好,语文课文一般要背,一般读两遍就能背下来,有时和同学比赛,拿一篇不长的新课文,读一遍也能背下来,错得很少。读书是要点天分的,不管学文还是学工学理,你的记忆力不好,书是读不好的,因为考试其实就是考你的记忆力,就是记忆力比赛。
小学读了一年,就算毕业了,又回到了农村。父亲没有打算再让我继续读书,而是在家务农。那天,我在稻田挂田埂,听小学毕业的同学说,如果再不报名,明天就截止了。于是我放下挂耙,直接去了零陵。我家到零陵是50里,吃晌午饭时我赶到了零陵一中。下午待老师上班后,我把名报上了,这已经到了下午4点左右。我未停留,又往回赶,天黑两三小时后,我才回到家。
考试时,外公给了我2元钱,量了两升米,我同复华公公去了零陵,头一天我们住在大西门旁边一家客栈,住一晚5角钱,在客栈搭伙煮饭,两餐也是5毛钱,菜是自己带的腌菜。半天考三门课:语文,数学,自然常识。考完就回家了。
大约半月后,考试发榜了,我考上了,复华没有考上,他复读一年后才考上。事后知道,我的语文是90多分,数学80分,自然常识不及格。我的作文得了最高分,而自然常识包括历史、地理和生物方面知识,而我过去上小学是插班,有许多东西没有学过。这次升学考试应该是幸运的。既然考上了,在外公外婆和奶奶的支持下,父亲作了让步。
送我读书,外婆是最早的倡导者和坚定的支持者。她对我外公说:“德根还是个小伢崽,哪做得事,他们家那点田,我们都帮他种了得了。读点书,将来吃碗轻巧饭。”
读书,是为了跳出农村苦海。读书,是为了吃碗轻巧饭,这就是我读书的目的。
进入零陵一中,那是另一个世界,我感到无比快乐和幸福。我在一中的学习成绩是中上,不是最好。主要原因是我把主要时间用来看小说。在农村辍学的四五年时间,主要是干农活,文化生活极为贫乏,一是没有书看,二是没有时间。当进了学校图书馆,看到有那么多书,特别是小说类。因此,除了上课的时间和规定必须参加的集体活动外,其他时间都用来看小说。我国的古典名著和国外的一些名著,以及当时流行白话小说都是这个时候看的。书看得很快,一般几天就一本,一个星期去图书馆借两次书。有时上语文、历史、地理课时也在书桌下面偷着看。假期,常从语文老师那儿借几本书拿回去看。因为我的文章写得可以,教语文的王立宾老师很喜欢我。有时,看古典小说,有些文言文不懂,常当面去请教,他很高兴地为我作解。
学习不拔尖还有一个原因,有一个学期我因吐血几乎不能上课,耽误课较多,靠自学而幸免留级。吐血的原因是在农村干活过重,当时年龄小,因劳致伤。每天吐血一两口,持续了两个来月时间。
知道我吐血的只有祖母一人。那天她去冷水滩姑母家,路过零陵,她来学校看我。我当时在宿舍躺着看小说。她知道我当时吐血,很是担心。我安慰她,没关系,医生说很快就好,她也相信了。临别时,她给了五角钱,说这是我姑姑给她搭船去冷水滩的钱,她决定走路去,不坐船了,省下这五角钱给我用。
一个老人自己没有收入,但只要自己还有一点力气,即使走四五十里小路,也要省下这五角钱,给自己生病中的长孙买点零食吃。当我接过被老人的手捏得汗湿湿的五角钱时,我无言以对。
应该说,在零陵一中上学,我的生活和经济状况还是比较好的。当时父亲在农村当小学教员,学费和吃饭是有保障的。另一个可靠的经济来源是我的外公和舅父。外公是一个地道的农民,但他能给牛看病,算得上是一个赤脚兽医,一年也有些收入。我舅父已从农村去了供销社工作,就是购销农产品,他有时也接济一点。
在零陵上学时,没有脸盆和蚊帐,夏天的蚊子和臭虫比较难对付。我们睡的是双人木制床。南方臭虫多,人被咬了以后起疙瘩,奇痒无比,非常难受。50年代,中央号召除四害中就有臭虫。在零陵一中消灭臭虫的办法是将整个双人床放到开水锅里煮,那真是一个创造。将两口很大的锅并列砌起来,在锅台上砌一个比双人床还要大一些的水箱。当熊熊大火把水箱里水烧开后,就把偌大的双人床放进去,煮上七八分钟,再抬出来。抬进抬出是要花力气的。放进去时,木床是干的,较轻,煮后木床浸水饱和就重了许多。要不断加水,火要不断“熊熊”,抬进抬出是很费一番周折的,此项工作学生要全程参与。
臭虫的生命力很强,传播的速度也极快。木床经开水煮泡后,一两个月内睡觉还是比较舒服的,感觉不到有臭虫,但时间一长,又有臭虫出来咬人了。照说臭虫煮死了,怎么还有呢?问题是煮床没有把所有臭虫都煮死。有的臭虫钻进木床一些裂隙深处,而把木床放进开水锅里时,速度往往较快,裂隙中的空气并没有完全被排出,热水不能进入裂隙深处,藏于深处的臭虫并没有被开水烫死。那些经过煮床而大难不死的臭虫们,经过重新组合,传宗接代,很快又繁殖起来了。
煮床不能一劳永逸,所以学校每年都要煮。臭虫咬人最猖獗的地方不是零陵,也不是长沙,而是武汉。1959年暑假期间,我从长沙去武昌看我的堂叔濮雅。他是我三祖父的小儿子,比我大两岁。当时他在华中农学院读书,临近毕业,我们已三年多未见,我将于1960年毕业,今后天各一方,难得再见面了。生活就是这样,自武昌这次见面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至今已60年了。
我们叔侄在武昌会面的时间极为短暂,都是臭虫造成的。武汉素来有全国三大火炉之一的称谓。我是八月初乘火车由长沙至武昌,到时已是傍晚,虽然太阳已下山,但天气闷热异常。在车站不远的一个国营旅社住了下来。一间房里摆了4张双人床,可以住八个人。但那天只有我和一个老者住那间房。老者六十开外,面目和善,红光满面,话语不多。由于热,我冲了好几次凉,才去睡。老者早已入睡。虽然闷热,为了不影响老人家,我未开灯,摸着床睡下了。毕竟是年轻人,很快我就入睡了。在睡梦中,我被蚊子和臭虫咬醒了,我感觉两手和脊背上都起了疱,且越来越多,越来越痒,以至于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于是我摸黑爬起来,没有开灯,走到外面的澡堂淋浴室,用冷水冲了大约二三十分钟,然后回到宿舍,拿出一件衬衣把头和上身盖起来,以防蚊子叮咬。大约过了十来分种,处在一种似睡非睡的状态中,感觉到脊背痒,有小虫子在上面爬,且越来越痒,奇痒,而后是一种灼痛。用手触摸,好像皮肤肿了起来。于是我开了灯,眼前看到的情景使我大吃一惊:凉席上,床架子中到处是臭虫,如同蚁群一样,密密麻麻,排成长队忙于逃跑——臭虫怕光,它们只在黑暗中吃人血。凉席上,身上到处是血迹斑斑,脊背、手臂上已不是一个一个的包,而是包连成了一片,皮肤增高了两三毫米,上面有不少血迹,是臭虫咬我的血和我在黑暗打死臭虫的血混到一起,真是恐怖!我脱光了衣服,用自来水冲洗了半天。天一亮,我就离开了旅馆。
老者仍未醒。昨晚我折腾了那么久,他也未醒,也未起来,似乎睡得很踏实。很长一段时间,我对老者的忍耐力,或者说他对蚊子和臭虫的抵抗力,我感到吃惊,并由衷地佩服。
如此功夫,实在难得。
由于事先没有联系,当我找到华中农学院,雅叔当时正在开会,办什么学习班,两三天后才能结束。他要我自己先玩几天,待他学习班完了再陪我玩。当时天气闷热,汗流浃背,一想到昨晚的蚊子臭虫,玩的兴趣早已云飞天外了。太困,我在他床上睡了一觉,中午在小饭馆吃了饭,我就直奔武昌火车站,第二天天亮时,我回到了长沙。
在武昌遭遇到的臭虫攻击,可谓终生难忘,每当想到当时情景,就毛骨悚然!
年青时,都希望离开农村,和现时的农村青年一样。农村是一个苦海,什么时候能游出来,能爬上岸,是当时的梦想,也是我外公外婆和我奶奶为我努力斗争的目标。几十年来,我想不通的是,父亲为什么要求我种田,他自己却没有种田,也没有种过田,最后还出去当了小学教员。谁都知道农村苦,千方百计要让自己的孩子去读书,将来有个好的谋生手段。但父亲不这样做,我们兄弟姐妹六人,没有哪一个是他主动送去读书的,有的妹妹小学都未毕业。
父亲给我们讲,我们先辈就是种田的,言下之意我们也可以去种田。但他还给我讲过,我的曾祖父种田发家后,为自己的儿子做的两件事:读书和习武。
曾祖父生了六个儿子两个女儿,重男轻女,虽只有两个女儿,结果把一个女儿很小时就给了别人做了童养媳。对六个儿子的希望却是让他们读书。我大祖父是江汉大学毕业,其他五个祖父都是高中毕业,因家庭经济所限,我祖父(老二),四祖父、五祖父和大伯父都上了黄埔军校,在抗日的战场上撕杀,四祖父还牺牲在抗日战场上。据我父亲讲,在送我祖父们去读书的同时,曾祖父还注意到对其身体锻炼和自卫能力的培养。他从祁阳请了一位武师,来家教我们祖父的拳脚功夫。曾祖父是一位地道的中国农民,少年、青年时代家中很苦,还租富人家的田来种,以后通过自己的努力发家了,到晚年家中殷实,已有数十亩水田。他不识字,没文化,但他懂得一个道理,一个人要想有出息,一定要有文化,所以他借钱也要送儿子去读书。为了不受别人欺侮,要有健康的体魄,一定要学点拳脚功夫,这是一个地道中国农民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
但我父亲只知道先辈们种田出身,但他没有深究,没有文化的农民是受人欺侮的,没有文化的人永远是最下层的人。由衡阳回到零陵农村,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为吃饱肚子而受苦。如果继续在农村呆下去,我可能也早已不在人世了,我生母去世时不到卅岁,我祖父母去世时还不到六十岁,我外公外婆也仅活了六十多岁,人的寿命与生活质量密切相关。
在零陵一中,我最大的收获是读了许多书,都是历史类和文艺小说类。那时,我的记忆力相当好,老师教的几门课可以说我从来不复习,课外时间就看课外书。我不追求考前几名,只满足差不多,大量时间用来看各种课外书。暑假回家帮助做农活,寒假农活少,有时间也是看书。
初中毕业时,我的班主任是教语文的王立宾老师,因为我的作文写得比较好,平常很喜欢我,劝我继续读高中,将来学文学。但当时家庭人口多,经济困难,还是决定去读不要钱的中专。
升学考试是在零陵考的,我报的是长沙水力发电学校(这个学校后来改名为湖南电力学院、湖南水利水电学院、长沙电力师范学院,现名为长沙理工大学),半个月后,收到了通知,被学校录取。我与舜球提前一天到学校报到,我同舜球分到同一个班——地质四班,全名是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专业第四班。这时,我们才知道报考填表时,应该填报一个专业。
两三天后,我们才知道从零陵招来的学生有十多个。同在地质四班的还有老埠头的邓治国和冷水滩附近的唐健。与我家不远的排龙山罗家的罗哲浩分在地质三班,水市桥北边的罗纹分在钻探四班,同分到钻探班的还有高溪寺胡英,等等。我们这些家乡同学,在金盆岭共同学习生活,然后天各一方,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除了舜球以外,与其他同学几乎失去了联系,没有了来往。当过省文联副秘书长兼《楚风》杂志主编的胡英成了专职作家,30年后在长沙相见,他送给我几本小说集,以后还见过几次面,通过几次电话。其他的几位老乡有的早已作古了。
零陵来的同学事先都未报专业,报到后专业及班级的分配完全是由学校划定的。老实说,当时我们并不在乎什么专业,只要能离开农村,能上个不要钱的学校,不当农民就行了。为祖国而学习,学好本领,报效祖国,既是当时的口号,也是我们内心的愿望。
学校刚建,宿舍还没有建好,我们就住在教学大楼三楼的教室里。一个教室住几十人,睡的是木制双人床,我同舜球一直睡上下铺。铺的是一床稻草垫子,上面再铺一张芦草席。我盖的是一床薄而短的棉被,我记得棉被中的棉絮(北方叫网套)是我八岁时,我生母专为我做的。因为是小孩,故棉絮短而小,我一直盖着它,不论冬夏。十年后,我已是一个非常壮实高大的小伙子了,就显得非常短小了,常是盖到头,就盖不到脚。
冬天是不太好过的。我除了外婆给我做的棉衣外,我只有一条双层布的夹裤,直到我参加工作到陕西后,才穿上绒裤(棉绒裤),那时叫卫生裤,再后才穿上毛裤、棉裤。从未穿过袜子,除了家做的布鞋外,就穿一种胶底布面的“力士鞋”。睛天雨天,冬天夏天都穿它。夏天穿它不透气,脚出汗非常臭,冬天穿它非常冷。坐着听课,脚就冻麻木了。
当时,十个班的同学的境遇同我差不多,基本都是从农村来的,穿着行李和经济条件都是彼此彼此。所以,课间休息的十分钟,整个楼道和教室都是一片跺脚声。
夏天好过一点,虽然热一点,但过去在家乡农村有在毒日下“双抢”干农活的基础,倒也不感觉怎样,但夏天的蚊子和臭虫是比较难对付的。
最热的天气,多是假期的45天。在长沙的四年,除中途一次回家参加祖母的葬礼外,一直没有回过家。假期用于勤工俭学,现在叫打工。有集体组织的,也有个人行为。打工的活路一般是挖土方,挑河沙,推板车,都是围绕基建工作而展开的。
在长沙一带,叫岭的地方非常多,都是丘陵地带一个个山包,这些山包都是第三系红土组成,已有几百万年的历史,红土非常致密坚硬,要搞建筑,必须挖高填低,削成一层层平台。挖土方是非常费力气的。用的工具是有两个齿的锄头,非常重,估计在15至20斤之间。虽然我们在农村干过农活,但一天到晚挖土方,还是辛苦异常。我们常常光着赤膊,穿条短裤,肩膀上搭一条洗澡毛巾,用来擦汗。夏天的长沙,太阳很毒,刚开始,一个个被晒得红肿,脱皮,时间长了,皮肤被晒成古铜色,油光闪亮。夏天碰到雷阵雨,雨水滴落在皮肤上,成圆珠状滚落,皮肤不沾水。开始挖土时,手掌会起泡,虎口常震出血,时间长了,手掌会长出一层硬邦邦的老茧,那时,就不感觉痛了。开学上课后,手上的茧皮就逐渐软化、退去,到下一个假期,这种情况又会重复出现。
挑河沙就是把船上装的河沙挑上岸来,再用车运至建筑工地,用来盖房或铺路。一担河沙一般100多斤,对我们这些在农村干过农活的青年来说,不存在困难。问题是从船上到岸上要经过一段用木板搭成的“桥”,木板较薄,又较长,刚度不够,挑着重担走在上面,忽闪忽闪,上下摆动幅度很大。刚开始都不敢走,要有人扶着才敢迈步,时间长了,也慢慢锻炼出来了。
挑上一天河沙,肩膀红肿,腿脚酸痛,收工往回走的力气都没有了。
推板车,也是一项挣钱的勤工俭学活路。不过,我干得较少。它不是集体活动,往往是两三个人,甚至一个人去干的活。一般选择在公路较陡的路段,为那些拉货物,主要是拉建筑材料,如砖瓦、河沙、木料、钢材的苦力们,帮助他们推车上坡,往往会费九牛二虎之力,搞得浑身冒汗。费用没有定例。有的在上坡推车前讲好价,但多数是不讲价,只问一下拉车的:“要不要推?”如拉车人说:“推!”你就帮他把车推上坡,拉车人会给你一毛、两毛钱。也有时把车推上坡以后,拉车人对你说:“对不起,同学,我身上还没挣到钱!”对我们来说,只认自己晦气,但也能理解,他们也是苦命人,就算帮个忙吧!反正年青人有的是力气。我外公常对我说:“小伢崽,莫懒,力气是用不完的,睡一觉又有的。”“力气越用越大。”这是真理。
上述三项活动,干一天可以挣到一块钱左右。我不喜欢推板车,因为每推一次,就要跟人说一次话,打一次交道,有时推了车,还得不到钱。挑河沙往往是一天一结,或者挑完一船一结,因为多是集体作业,有班上的劳动委员管此事,不用自己操心。挖土方可以是集体的,也可以几个人合作,去工地包一块地段,挖几天,甚至挖二三十天,干完活再结帐。一天干多少时间,早出工,还是晚收工没有人督促,较为自由。一般挖土与挑土是连在一起的。舜球与我经常在一起打对子。我俩往往是挖土挑土换着来,这样干起来比较轻松。我的力气比他大,但韧性不如他。
这些勤工俭学劳动,对于我们这些从农村来的小伙子来说,倒不怎么觉得是苦差使,与农村比起来,至少有两大不同:首先是干活时间短,不像农村一年干到头。特别是夏天双抢期间,天不亮就起床,去割禾打禾,天黑后才收工。第二,能吃饱肚子。本来我家是江南鱼米之乡,1950年土改时,我们那儿农村,平均每人可分到一亩半水田,三分旱地,山地更多。本来不愁吃,不愁喝,所谓喝,就是喝酒。我们家乡农民都兴自己酿酒喝,家家都会自己酿酒。大米,小麦、红薯、柿子都可酿酒。自己酿酒自己喝,先吃甜酒——北方叫醪糟,甜酒老了,不甜时,再放进泉水,泡一段时间,吃水酒。水酒老了,就熬制烧酒——北方叫白干。我的几位堂弟,现在每天中餐晚餐都要喝上几杯,按他们说法,现在我天天有肉吃,餐餐有酒喝,幸福得很。在农村,就吃的来说,鸡鸭鱼肉不断,这些都是自己种养出来的。
但从1951年开始,我们那儿就吃不饱肚子了。农村实行统购统销,农村干部为了表现自己积极,争先进,各个区乡都争着多卖粮,最后愈演愈烈,秋收完,卖完粮,家家的粮仓都空了,所谓放下镰刀没饭吃。开始吃统销粮,瓜菜代的苦难生活。
1955年,我们邻省由于浮夸风,大卖余粮,最后饿死了不少人,中央最后做了处理,枪决了几个,形势有所缓和。但我的家乡并没有大的改观,当时盛行“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仍然是卖多留少,大家都吃不饱肚子,更别说荤腥油水了。
到了1960年,全国都很困难了,吃不饱的现象已非常普遍。但在学校有一位令我尊敬,至今难以忘怀的管后勤的校长,是他让我们吃饱了肚子。他是一位老红军,13级干部,小学文化程度。对工作极端负责任,对我们这批从农村来的学生,倍加爱护。当其他学校已开始定量供应粮食时,他亲自跑粮食局,找战友,拉关系,为我们搞到一批碎米,因碎米不算定量。他叫厨房把碎米和好米混到一块做,这样,直至1960年8月我们离开学校时,吃饭是不限量的。他认为,年轻人是长知识,也是长身体的时候,不吃饱饭怎么能行呢!旧社会才吃不饱肚子。他对当时形势的认识还相当模糊,但心肠之好令我们感动。
在长沙的学校生活,是艰苦的,也是快乐的。学习对我来说是轻松的,我的记忆力好,应付各类考试还是轻松的。但我几乎没有经济来源。吃饭是助学金,书本是学校发,但笔墨纸砚和穿着及生活花费都得靠自己。除了劳动获得一些收入外,家里很难支助我们。在学校这段时间,有两个人给予了我帮助。一个是我的堂兄濮俊,我大伯父的长子。解放后不久,他参加了供销工作,开始在衡阳,以后去了江西工作。1957年他路过长沙,他来学校看我,我们有五六年没有见面了。见面后,似乎没有多说话,我只记得他说过这样的意思:好好读书,要跳出农村这个火坑。临别时,他给了我10块钱。此后,我俩再也没见面,他于80年代去世,据说生有两个儿子,但从未见过面。
另一个同学,也是我的老乡叫罗纹。他学钻探工程,于1958年提前毕业参加工作,后改行学机电安装。1959年暑假期间他在湖南水府庙水电站搞安装工作,他约我去耍。我到他那里后,他与同班同学戴丽华结婚了。他俩热忱地接待了我,在那儿玩了几天。临别时,他们赠送了我15元钱。在当时可能是他的半个月工资。
俊兄和罗纹共赠我25元,就当时而言,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解决了我的一些困难。我最困难的一个学期是1959年上半年,那学期我只花了8分钱——给家里寄了一封信,买了一张8分钱邮票。那封信还不知道家里收到没有,因为至年终我都没有收到家里回信。那个学期,我没有出过校门。
就学习考试成绩而言。头一两学年实行5分制,我一般都是5分,很少得4分。我在班上当过体育委员、劳动委员,以后几年当过学生会的学宣部长。我写文章出手快,也带一点鼓动性。1961年我已在陕西工作,从母校那里得到一个信息,说刚进学校的一年级同学骂我,说上了我的当。他们看了我在1960年写的一篇文章才考电力学院的。我的那篇文章,后来被学校摘录在招生简章上。
学宣部长主要管学习和宣传,这项工作比较琐碎繁忙,出版报、壁报,油印刊物,还有一个广播室,要组织和审查稿件,安排广播,这些都由学宣部管。除组织各班学习委员和通讯员写稿外,有些稿件还得我亲自执笔。宣传工作由党委宣传部管,学习方面由教务处管。这两项工作占去了我许多课余时间。只有到了每个学期期末,复习考试时那两周时间,才算轻松一阵子。
有一天,党委宣传部一位老师找我,说宋校长找我。于是我很快去了宋校长办公室,宋校长很热忱地接待了我,叫我坐下,并叫通讯员给我泡了一杯茶。这是一种很高的待遇,很少见到在办公室里,老师(领导)给学生泡茶喝的。坐下后,他首先问了我的学习情况和学会的工作情况。接下来就讲开了政治,他强调作为一个干部,一定要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明确的政治方向。“你很不注意政治立场问题,工作粗糙,你犯了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
听了他的话,我感到非常吃惊,我究竟犯了什么错误?性质如此严重,我等待他下文。
“校门口贴的标语是错误的。”他有点生气。我马上想到校门口贴的一幅对联式的标语:教育为政治服务;教育与劳动相结合。没有错呀,但我没有吭声。
“你写的政治是无产阶级政治?还是资产阶级政治?”
我恍然大悟,马上认错,没有顾得上喝茶,立即去了校门口,将两条标语撕下,并换下了如下两条标语:
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不久,学校安排去农村参加“双抢”劳动。“双抢”即抢收抢种,是农村农活最忙的季节,政府部门一般都要安排学校学生参加这一活动。学校党委安排我随宋校长一起行动,以便了解一些情况,便于写报导和总结。
下乡第二天,我就写了一篇报导,拟送省报发表。内容是讲学校非常重视这次“双抢”活动,教职员和学生们如何积极响应参加等情况。写完后,我请宋校长先看。他看了以后,没有说话,却叫党办主任给他找当天的《人民日报》和《湖南日报》。报纸送到后,他坐在那儿看起来,把我晾在一边,也不同我说话。过了一会,他才把我叫到他跟前。
“濮声荣你看看,别人写的报导。”他指着报纸上的一篇文章对我说。
“在党的领导下,怎么怎么行动。”
“首先是党的领导,然后才会有行动,首先有党,才有成绩。不听党的话,才会有错误,才会失败。”
“人家写的第一句话,是在党的领导下,切入正题,突出重点……”
这是我听到的最好政治的话,政治宣传活动中的精髓,是评价事物和看待问题时,首先必须想到的。他的这段话,使我终生受用不尽。特别是搞文字工作,广众场合讲话的人,如果不知道这个原则,肯定会碰壁一生。
在长沙四年,虽然寒暑假都不回家,但除了在学校生活外,很少去长沙各地走走。我记得就是1958年暑假去过一次岳麓山,1960年毕业后同舜球又去过一次,其他地方都没有去。1958年到南郊修过铁路,到新开铺一带抓过老鼠和麻雀——参加除四害运动。上岳麓山,必去岳麓山书院参观。这是有名的中国四大书院之一。岳麓书院现为湖南大学范围之内。大门的正上方悬挂宋真宗书写的“岳麓书院”的御匾。大门两旁有副非常霸气的对联:
惟楚有材;
于斯为盛。
在以后几十年的南来北往旅途中,常有人提起这副对联,它成为湖南文人的一张名片。其大意大致了解,但对其真意及其出处不知所以然。当退休后,再次游览岳麓书院,见到《岳麓书院》一书时,才知其来由,书中如此介绍:
“相传清代嘉庆年间,书院进行大修,完工之后,门人请山长袁名曜撰写对联。山长以“惟楚有材”嘱诸生应对,众人苦思,不得其果。贡生张中阶至,脱口答曰:“于斯为盛。”
联为流水对,意思是说楚国(特指湖南)人才众多,而书院尤为兴盛。上联出自《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虽楚有材,晋实用之”,下联出自《论语·泰伯》:“唐虞之际,于斯为盛”。
这副对联,正是岳麓书院千年以来,人才辈出的真实写照。特别近现代表现出的伟人更是突出,名人甚多,可数几箩筐。
岳麓书院悬挂有多副对联,寓意深远,给人印象深刻的有两副对联,其一是:
工善其事,必利其器;
业精于勤,而荒于嬉。
其二是:
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陟岳麓峰头,朗月清风,太极悠然可会;
君亲恩何以酬,民物命何以立,圣贤道何以传,登赫曦台上,衡云湘水,斯文定有攸归。
前联为学人必须遵循的要领和精髓,后联为做人应具备的积极的人生态度。都蕴含深刻的人生哲理,值得吸取和时时玩味。
上述两副对联是我第一次参观岳麓书院记下的,后记录在笔记本中,笔记本已发黄破旧。
毕业临别时,我同舜球再一次上了岳麓山。那次看的地方较多,舜球还带了卤肉和葡萄酒,我俩在山上聊了一天,天黑才回到学校。
与舜球的这次长谈,对我以后走上社会,学习生活工作影响深远,似乎才明白一些事情。例如,学习没有必要去争前几名,尤其是第一名。把要学的东西搞懂了,搞通了,会用了就行了,没有必要死记硬背。学习还应广博,不局限某一门学问,将来干什么就钻什么。搞运动的时候,不要先发言,发言尽可能使用中性语言,对事对人要永远一分为二,不清楚的事不要轻易表态。对人要坦诚,要厚道,不要议论和评价第三者,不要轻信,要同情弱者,不畏惧强者。
然而,在以后的生活中,我也想做好点,但许多没有做到,还是性格使然。
学校各种社会活动还是比较多的。1959年我受到了班上团支部组织的批判,说我骄傲自满,个人英雄主义。起因是我跟一位刘姓同学闲谈时,说过这样一段话:学技术,要经得起孤单,耐得住寂寞。十年磨一剑,只要你有真本事,迟早会被社会重用的。有如金子,即使埋藏沙砾中,迟早也会闪光的。
批判的重点是:你为什么说自己是金子?别人是什么?他们都是砂砾?你怎么这样骄傲,疯狂到了极点!
开始我想不通,我说的一段话有什么错,我说话的前提和中心思想是什么?我这是说的励志的话。但当时,我不能说话,任凭大家反复分析批判,上纲上线,前后开了三次会,我检查了三次才过关。幸运的是没有给我处分,也没有建议学校免去我的学生会学宣部长。
为这个事,舜球很为我不平,他对我讲了很多大实话,以及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的警言。对我来说,真是受益匪浅。这为我踏入社会数十年的生活,没有吃大亏,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也使我认识到人性险恶和祸从口出这一千古遗训的正确性。
话虽如此,但在文化大革命开始阶段,我被一位王姓同学出卖了。
运动刚开始时,队上有人贴我的大字报,但不多,那时我任地质分队长。大字报说我走“白专道路”,不突出政治,是反动技术权威。但时隔不久,运动发展到“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我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自然不是重点,靠边站了,仍然叫我抓队上生产。
这个时候,从母校给我们院发了一个函,说我是学院黄修本的嫡系高材生,而黄是三家村黑线上的人。要我主动揭发黄的反动言论和罪恶勾当。当时,我带队在陕北三边地区搞水文地质勘探,找水救灾,我当即返回队部。院队领导找我谈话,希望我划清界线,站稳立场,主动揭发。我能说些什么呢?黄校长是民盟人士,一直很受同学爱戴,他主管教学,而我是学生会学宣部长,与他接触较多。毕业时,党委想留我在党委宣传部工作,而他想留我当教师,我都谢绝了,我是最后分配到陕西来的,最后把舜球和另一位蔡姓同学留下当教师。
到陕西后,我同黄校长通过几封信,主要说来陕后的工作情况。他写给我的信,我还保留着,于是我找出那几封信,并写了一点揭发材料,交给院党委,转交母校。揭发的材料主要写了两条:第一,不突出政治;第二,他对学生的穿着要求是资产阶级的,例如,他要求学生穿衬衣,必须把衬衣的下摆放到裤子里。原始信件是很能说明的。所以,学校造反派再也没有找我的麻烦。
1967年初,全院集中到西安院里搞运动,我担心有人又会提出我跟黄校长的关系。于是,到西安后,我向与我一块分到院的同学说,如有人提及此事时,希望能帮忙解释一下。有一位王姓同学平常跟我关系不错,当我提出这一希望时,他非常爽快地答应:“冒问题!”一口地道湘乡话。
第二天在院里,以室、队为单位学习文件,进行批判。当时批判的重点还是“三家村”,“地富反坏右”的代表人物,“牛鬼蛇神”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会议开始时,较为冷场,没有人发言。地勘队工人多,文化程度不高,批判不知从何说起。这时,主持会议的领导,进行启发鼓动,要求大家结合院内的人和事,进行揭发批判,干部要带头,要争取火线立功,火线入党,这是生死存亡的斗争,是党和毛主席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然后,领导大家呼口号,这时群众开始骚动,情绪有所激动。
就在这时,我的这位同学突然站了起来,很是激动,大声叫道:“我要揭发!濮声荣是三家村黑线人物!”他的话说出后,会场上是一片宁静,很多人都露出了惊讶的表情,我也惊呆了。
这位同学说,昨天晚上我去找了他,叫他不要说我和黄校长的关系。现证明黄修本(即黄校长)是三家村里的黑干将,而濮声荣是黄修本的黑干将,他过去写过文章,宣扬封资修,他们是一条线上的人,肯定有鬼。如果没有鬼的话,为什么叫我包庇他?现在叫濮声荣老实交待他与黄修本的关系。还有,他写过哪些宣扬封资修的文章,叫他交待。这位同学越说越激动,涨红了脸,口角出现了一些白色泡沫。他说完后,会上又是一片宁静。因为事情太突然,因为一块分来的五位同学中,我表现比较优秀,又当了地质分队长,平时跟大家关系不错,而说的事情是过去学校老师的事,离他们很远,所以,大家不知怎么说才好,因而冷了场。
冷场一段时间后,还是主持会议的领导,叫我说说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刚开始说时,我觉得非常突然,不可理解,我们都是同学,从南方鱼米之乡来到这不发达的北国,平常关系还很不错,应该相互关心,相互提携才对,怎么在关键时刻捅刀子,说一些莫须有的事呢?!
这时,我已变得非常冷静,况且在群众场合说话,我已锻炼出来了。于是我简要介绍了前段时间,母校来函要我揭发黄校长的罪行。我同黄校长是一般师生关系,因为我当过学宣部长,与他接触多一点,我分配来陕西工作后,相互通过几封信,信的内容可以证明我们之间的关系,这些信我已交给了组织。我说完后,没有人质疑和指责,会场又冷了下来。
没有人说,我倒主动说开了:既然王同志说我同黄校长是黑线上的人,写过许多文章,他可以揭发。另外,一块来陕西还有几位同学,他们可以作证,也可以揭发。我还说明,我自离开学校来陕西工作后,从没有写过文艺方面的文章,我连小说都不看,大家可以作证。
我后来的一点补充说明,是很有说服力的。不论是工人、干部,他们没有见到我看过小说,打过扑克、麻将之类。除了工作之外,其他时间都是看业务这方面的书,我还订过几份业务杂志,是一个走“白专道路”的人。
没有人说话,时间也快到了吃饭时间,于是散会。
王姓同学想表现积极,企图争取火线入党,但他的揭发没有人响应,其他同学都表示沉默,他落了个自讨没趣,文革后期他就要求调回湖南老家了,不久他妻子去世,似乎一个人生活。
这就是我的学业梦。“梅花香自苦寒来”,完全是“苦”出来的。可以说,比古人还苦。为什么?因古人只有富家子弟才有资格上学。解放后,我们穷苦孩子可以上学了,但经济上并不富裕。所以,“寒窗之苦”和“羞涩之苦”,岂不是古人的双倍么?
但我发现,只有“苦”出来的学子才有用!纨绔子弟有几个中了状元?更别说国家栋梁之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