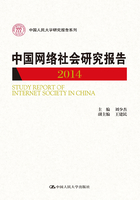
一、社会认同研究的转变与限制
社会认同是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核心问题之一,虽然很多学者在20世纪前期就已经对社会认同开展了大量研究,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讨论社会认同的文献仍主要是关于个体自我认同的,诸如关于个体的身份认同、群体归属、地位和层次认知等,都属于通常的社会认同研究。因此,一些社会学家认为,20世纪前期的社会认同研究实质是个体认同研究,真正从社会层面开展的认同研究开始于20世纪60或70年代。特纳曾明确指出:“社会认同论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转引自 [澳]豪格、[英]阿布拉姆斯:《社会认同过程》,前言,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93162A/146765440058481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48468915-KRhYJDQvRBMmhD6Kz4YBRo8IRP8dcACt-0-616dc19eb9a6620010cd7173cd44bb3b)
方文论述了社会认同研究在社会学心理学中发生的从个体向社会的转变。方文认为,在1967年,社会心理学发生了两个重要事件:一个事件是被誉为“社会心理学教皇”的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1919—1989)厌倦了个体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导致了“社会心理学危机话语”的发生;另一个事件是泰弗尔(H enri Taifel,1919—1982)和莫斯科维奇(Serge Moscovici,1925—)举起了“社会关怀”旗帜,开始了群体认同或群际认同的研究。这两个事件共同宣告了个体论的社会认同研究的突破。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社会认同研究从个体向群体乃至社会的转向,虽然应当看到是通过心理学家研究方式的转变而实现的,但这种转变为什么是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发生的?事实上,20世纪60年代后期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为这个转变提供了重要的现实基础。1967年,丹尼尔·贝尔发表了《关于后工业社会的札记》,同年加芬克尔出版了其代表作《常人方法学研究》。笔者曾指出:“贝尔以后工业社会理论直接概括和揭示了科技革命引起西方社会的深刻变化,而加芬克尔则是以社会学思维方式变革的理论主张和原则建构,间接地表达了对科技革命引起社会变革的理解和体验。” 费斯廷格、泰弗尔和莫斯科维奇等人在心理学领域引起的转变,其实同贝尔和加芬克尔的研究一样,都不过是对科技革命推动后工业社会来临的一种学术反映。
费斯廷格、泰弗尔和莫斯科维奇等人在心理学领域引起的转变,其实同贝尔和加芬克尔的研究一样,都不过是对科技革命推动后工业社会来临的一种学术反映。
由科技革命推动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之所以能够促进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突破个体论限制,最重要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两点:其一,后工业社会实现了产业结构转型,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大幅度下降,而第三产业的比重则迅速上升。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已经达到70%以上。产业结构的这种变化表明,面对物或面对自然的物质生产地位已经下降,而为人服务的第三产业已经上升到主体地位,因此,发达国家的中心任务已经从物质生产转移到为人服务。物质生产处理的主要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第三产业或服务业处理的主要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这种变化必然要求人文社会科学超越个体论的视角,切实从社会关系的视野观察和研究社会生活。
其二,更为重要的是,推动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变迁的技术革命是信息技术革命,以计算机为核心的信息技术革命,不仅大幅提升了信息传递的速度和规模,而且还极大地扩展了人类信息交流的途径和空间,提高了社会交往的地位。信息技术革命以其不可遮挡的魅力,把越来越多的人从狭小的个体活动场所带入广阔的社会交往领域。各种场所中的群体活动,甚至超越群体界限的、在更广泛层面上的信息交流,都呈现了信息技术革命之前无法实现的活跃状态。人们通过日益便捷的信息交流或更加广阔的信息空间,不仅能够更清楚地认识他人,也能更明确地理解自己。原来在工业社会和农业社会局部空间中不易判明自己身份归属的问题,变成了如何在复杂的信息交流中认识群体乃至认识社会。
因此,社会心理学对社会认同的研究从个体论转向群体论,其原因不能仅仅归结为研究者的心理变化和视角转变,更重要的是社会现实发生了深刻变迁。并且,社会生活网络化的发展,更明确地从现实基础出发,要求社会认同的研究实现转变。时至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和手机通信等新媒体技术迅速发展,这使信息技术革命形成了更加波澜壮阔的局面,社会生活实现了大规模的网络化变迁。人们在网络化潮流中涌入越来越广阔的社会空间,城市社会、民族社会乃至全球社会,人们可以凭借新媒体技术便捷地进入其中。在不断扩张且充满新因素和不确定性的网络社会中,重要的问题已经不是自我属于这个社会的哪一个位置,而是自我应当怎样看待和评价这个瞬息万变的新型社会。
卡斯特是对网络社会开展了深入研究的学者,在他看来,网络社会是一种与工业社会在农业社会中崛起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新社会形态,而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以互联网和手机通信等新媒体为基础的社会认同的转变。卡斯特在《认同的力量》中开篇就指出:“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生活,正在被全球化和认同的对立趋势所塑造。”![[美]卡斯特:《认同的力量》,1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93162A/146765440058481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48468915-KRhYJDQvRBMmhD6Kz4YBRo8IRP8dcACt-0-616dc19eb9a6620010cd7173cd44bb3b) 之所以把认同与全球化看成一种对立趋势,并坚持在这种矛盾关系中审视网络社会崛起引起的各种社会变迁,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全球化是新自由主义和西方各国政府推进的“战略决策性经济活动”
之所以把认同与全球化看成一种对立趋势,并坚持在这种矛盾关系中审视网络社会崛起引起的各种社会变迁,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全球化是新自由主义和西方各国政府推进的“战略决策性经济活动”![[美]卡斯特:《认同的力量》,1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93162A/146765440058481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48468915-KRhYJDQvRBMmhD6Kz4YBRo8IRP8dcACt-0-616dc19eb9a6620010cd7173cd44bb3b) ,它不仅引起了世界经济秩序新变化,而且也冲击甚至剥夺了广大社会成员的利益,各民族的基层社会成员形成了抗拒性的集体认同,抗拒性认同通过网络媒体实现了穿越传统社会制度的横向连接,并动员起激烈冲击全球化秩序的各种大规模社会运动,表现出抗拒性的集体认同是必将引起人类社会发生空前深刻变革的强大的社会力量。卡斯特兴奋地指出:“伴随着技术革命、资本主义转型、国家主义让位,我们在过去的25年里经历了集体认同强烈表达的漫天烽火。这些集体认同为了捍卫文化的特殊性,为了保卫人们对自己的生活和环境加以控制,而对全球和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提出了挑战。”
,它不仅引起了世界经济秩序新变化,而且也冲击甚至剥夺了广大社会成员的利益,各民族的基层社会成员形成了抗拒性的集体认同,抗拒性认同通过网络媒体实现了穿越传统社会制度的横向连接,并动员起激烈冲击全球化秩序的各种大规模社会运动,表现出抗拒性的集体认同是必将引起人类社会发生空前深刻变革的强大的社会力量。卡斯特兴奋地指出:“伴随着技术革命、资本主义转型、国家主义让位,我们在过去的25年里经历了集体认同强烈表达的漫天烽火。这些集体认同为了捍卫文化的特殊性,为了保卫人们对自己的生活和环境加以控制,而对全球和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提出了挑战。”
从卡斯特的论述中不难发现,他像泰弗尔等人一样重视的不是个体认同,而是集体或群体认同。然而,在卡斯特的论述中会发现,同泰弗尔不同的是,卡斯特实质上已经超越了泰弗尔的群体认同论视野,通常是在论述超出群体边界的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认同。虽然卡斯特一再强调自己论述的认同是与个体认同不同的集体认同,但他论述的集体是没有清晰边界的,吸引了不同民族、不同社会阶层以及不同工作职业的社会成员参加的社会运动。在社会运动中的认同已经不是泰弗尔仅仅超越个体认同的群体认同,而是凭借信息交流和网络沟通超越了各种集体边界的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认同。
这里面对的问题是,卡斯特为什么坚持用集体认同概念来表达实质上已经超越了集体边界的社会认同?这或许是主流社会学的结构论研究方式的限制。从涂尔干开始的结构论研究方式,虽然也重视对社会生活的整体性研究,但结构论的基本视角首先是注意事物的构成因素及其相互间的关系,或者说,实现结构论这个研究目的必须以弄清事物的构成要素为前提。正是基于这种基本原则,当卡斯特从结构论视角观察社会认同时,尽管已经认识到网络社会中的认同是可以超越各种边界限制的社会认同,但仍然总是在结构论视野中寻找社会认同的构成,而寻找的结果只能是个体认同和群体认同,难以看清整体意义上的社会认同。只有超越结构论的限制,才能从整体上把握突破了群体或集体边界的社会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