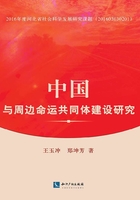
第二节 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现实依据
中国与周边国家经济文化的深度交融,将彼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在促进经贸往来的同时,也为恐怖主义、环境污染、经济危机、非法移民、走私问题、毒品泛滥与流行疾病等威胁的跨区域联动提供了条件。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加深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相互依存程度,在一系列日趋严峻的国际性问题面前,任何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恐怖主义、毒品问题、环境问题和发展问题等各种问题的跨区域联动交织,需要中国与周边国家通力协作、共同应对,是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现实依据。
一、构建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是反恐协作的需要
在全球化时代,恐怖势力的活动范围跨越国界相互勾连,已经演化成为区域性或全球性问题。恐怖主义犯罪对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安全和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威胁,东南亚、南亚、中亚、俄罗斯东南部地区和中国西部都深受其害。生存与发展问题的倒逼,迫使中国与周边国家联合起来,加强协商与合作、建立区域对话机制、消除贫困,以应对全球化时代恐怖主义威胁。
恐怖主义有反人类的共性,有造成社会恐慌的共性,有危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共性,这正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反恐合作的利益交汇点和重要推动力。中国的恐怖组织与周边国家的相互勾连,恐怖主义组织与极端主义组织的相互勾结使区域安全协作水平和能力面临新的挑战。中国与周边国家唯有对区域安全威胁形成高度共识,以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加强多边和双边安全合作,发掘更多的合作领域和合作空间,才能切实提高反恐合作的有效性。
二、构建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是禁毒合作的需要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面临的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毒品犯罪成为全球性公害。国际毒情的外溢蔓延,致使我国毒情愈加复杂和严峻。“金新月”和“金三角”位于中国周边,是世界两大毒源地,这两个地区的毒品问题已成为困扰区域稳定的“毒瘤”。毒品问题又衍生出艾滋病、武器走私、跨国犯罪等问题,毒品安全问题与社会问题共同混合、互相作用影响,威胁着区域国家的利益。全球性顽疾,需全球治理药方。毒品问题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命运连接在一起,贩毒集团的全球性、集团性与组织性,需要中国与周边共同发力,共同推进禁毒国际合作。
“金三角”位于泰国、缅甸和老挝三国的边境地区,是鸦片类毒品产销基地。中国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与“金三角”毗邻,有503.8公里边境线。中缅边境地区山水相连,村寨相依,无天然屏障。毒品犯罪分子便利用山间小道、沟渠小河等便利条件,以人体藏毒、货物藏毒和车辆藏毒等方式藏匿毒品,以人货分离、分段运输或绕道运输等方式运输毒品,将“金三角”所产的毒品由境外偷运至中国西南各省,再经广东、福建等省,转运至香港、澳门,复贩卖至东南亚国家和欧美发达国家。贩毒分子为获取高额回报,甚至不惜以武装对抗政府和国际社会的打击,严重威胁到相关国家社会安全。当前,“金三角”地区的毒品影响范围已蔓延至东南亚地区甚至整个世界,东南亚国家更是首当其冲。毒品过境国势必成为毒品消费国,东南亚地区吸毒人员增多,严重影响社会风气和社会治安,严重威胁东南亚地区的安全。同时,贩毒集团的势力日益壮大,其财力和对地区的控制力都在不断攀升,并呈现出与恐怖组织互相勾结的趋势,这都对东南亚及周边地区的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
“金新月”位于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伊朗的交界处,是鸦片和海洛因的生产基地。20世纪90年代,受民族冲突、宗教矛盾和战乱等因素的影响,“金新月”毒品影响范围进一步扩大,成为全球最大的鸦片产区。阿富汗是“金新月”毒品的主要产地,毒品经济已渗入阿富汗社会各个层面,并且与阿富汗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问题错综交织,使阿富汗成为“毒品”和“恐怖”共存的国家,成为令国际社会为之侧目的“毒瘤”与“恶瘤”。2012年,阿富汗的鸦片产量占世界非法鸦片产量的74%,海洛因产量已达世界总产量的80%以上。 毒品泛滥不仅造成了阿富汗的刑事犯罪、官员腐败和社会败坏,而且为恐怖主义提供资金支持,使毒品共生问题与其他社会恶性问题错综交织,构成了区域国家的复合性安全威胁。阿富汗前总统卡尔扎伊曾说过:“阿富汗有了和平,这个地区也有了和平;阿富汗陷入了麻烦,这个地区也就有了麻烦。阿富汗和平了,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也就终结了;阿富汗有麻烦了,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也将因此继续存活下去。”
毒品泛滥不仅造成了阿富汗的刑事犯罪、官员腐败和社会败坏,而且为恐怖主义提供资金支持,使毒品共生问题与其他社会恶性问题错综交织,构成了区域国家的复合性安全威胁。阿富汗前总统卡尔扎伊曾说过:“阿富汗有了和平,这个地区也有了和平;阿富汗陷入了麻烦,这个地区也就有了麻烦。阿富汗和平了,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也就终结了;阿富汗有麻烦了,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也将因此继续存活下去。” 毒品犯罪与暴力恐怖犯罪交织,销蚀着阿富汗社会,恶化着阿富汗安全局势,威胁着区域国家的安全与稳定。由于历史、社会文化与地缘的密切联系,与阿富汗接壤的中国已成为“金新月”毒贩首选的过境、集散和消费地。“金新月”的毒品问题与暴恐势力、黑恶势力和洗钱犯罪等问题相互交织,对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社会安全和稳定构成了极大威胁。
毒品犯罪与暴力恐怖犯罪交织,销蚀着阿富汗社会,恶化着阿富汗安全局势,威胁着区域国家的安全与稳定。由于历史、社会文化与地缘的密切联系,与阿富汗接壤的中国已成为“金新月”毒贩首选的过境、集散和消费地。“金新月”的毒品问题与暴恐势力、黑恶势力和洗钱犯罪等问题相互交织,对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社会安全和稳定构成了极大威胁。
毒品犯罪常引发其他犯罪问题,并溢出境外,形成跨境犯罪问题,破坏了相关国家正常的社会和经济秩序,给国际社会安定和治安管理带来严重危害。在禁毒合作方面,中国政府认真履行各项国际禁毒公约,积极参与各项禁毒国际活动,不断加强与相关国家进行禁毒政策沟通,在禁毒政策制定、缉毒执法等多个领域开展务实合作,对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禁毒工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禁毒警务合作机制还不太完善,禁毒效果还不太明显。解决全球化时代的跨国毒品问题,必须通过共同协商,国际社会互通情报、互相协作,切断毒品的生产与贩运链条,才能遏制和解决毒品问题,真正实现“禁毒命运共同体”层面共赢效果。
三、构建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是环境治理的需要
自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及周边地区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活跃的区域之一。伴随经济的快速增长,空气污染、海洋环境问题、土地沙化问题、化学品污染问题、跨境水资源问题等也日益突出。在区域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形势面前,中国与周边国家都是受害者。环境问题具有公共属性,生态环境恶化不是一国造成的,环境治理也不可能孤立地解决。环境问题和共同危机的出现,将国际合作提上了日程,共同安全、共同发展、共同治理等理念越来越成为各国政治家的共识。在环境问题面前,中国与周边各国命运与共,必须提高思想认识,在全球共同治理的制度框架之内通力协作,共同推进全球环境治理的长足发展,并以此避免“公用地悲剧”在中国与周边环境领域内的蔓延。
海洋是人类的重要战略资源和储备,对中国及周边国家的国土安全和经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滨海国家为了拓展生存空间,加速经济发展,都在加强对海洋的开发利用,海上石油勘探开采、海上运输、海洋捕捞等生产活动大大增多。海洋的容纳能力和自净能力都是有限的,相关国家在开放海洋的过程中排泄了大量的污染物,造成了海洋的严重污染,并导致了邻近海域的污染。在泰国,2009年与2010年城市污废水处理率仅有23%;在越南,75%的城镇家庭产生的生活污水没有进入污水处理系统,每天经收集处理的城市污水低于10%,且大部分城市排水系统均未实现雨污分流。 虽然环境问题已引起相关国家的重视,大多数国家都制定了海洋环境保护政策或法规,但保护海洋意识还不够强,海洋陆源污染防治机制还不够完善,中国与周边区域的海洋环境污染已成为环境问题中的重要议题。
虽然环境问题已引起相关国家的重视,大多数国家都制定了海洋环境保护政策或法规,但保护海洋意识还不够强,海洋陆源污染防治机制还不够完善,中国与周边区域的海洋环境污染已成为环境问题中的重要议题。
空气污染是中国与周边国家面临的又一重大环境问题。随着中国与周边国家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工业“三废”垃圾导致了严重的空气污染,燃煤独大的能源结构导致空气污染日趋恶化。大气污染物的扩散导致了跨区域的大气污染,还导致了大面积的酸雨污染。由于防污意识不强,区域国家均有相当数量的酸雨前体物排放,区域国家既是污染排放国,又是污染受害国。中国青藏高原以东、长江干流以南地区,是世界第三大酸雨区。中国61.8%的南方城市不同程度地出现酸雨,酸雨面积占中国国土面积的30%。朝鲜、韩国、日本、蒙古、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都处于产业化生产阶段,污染物排放量增加,跨境污染物也在增加。依据东北亚国家日益增长的煤炭消费需求来分析考量,东北亚地区的酸雨污染问题将更趋严重。
印度尼西亚是烟雾污染产生的根源地之一。印度尼西亚的森林火灾和废物燃烧引起了严重的烟雾污染,对东南亚地区的空气质量产生了重要影响。2006年,印度尼西亚森林大火烟雾笼罩东南亚部分地区上空,马六甲海峡的交通都受到了影响。新加坡媒体曾连续发文指责:由于印尼政府的无作为,致使印尼开荒产生的烟雾随着厄尔尼诺现象飘至新加坡,导致新加坡“霾季”的产生。另外,中国与周边区域的雾霾污染的程度也在逐渐加深,在一些地区,雾霾污染的严重程度已经超过世界卫生组织的警戒线,严重危害中国与周边国家人们的健康,治理雾霾已成为区域环境治理的重要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交流和人文交流的日益频繁,艾滋病、埃博拉出血热、SARS、甲型H1N1流感等传染病跨境传播的速度进一步加快,严重危及人们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甚至威胁到地区安全与稳定。传染病的跨境传播使公共健康问题逐步演变为全球或区域性的公共卫生危机。全球卫生的未来直接或者间接地与跨国经济、社会和技术变化相关联,公共卫生政策的国际国内空间被交织在一起。 2003年的“非典型肺炎”(SARS)疫情的跨境传播,对中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等国家人们的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对旅游、交通、餐饮等产业造成严重的冲击。经贸与人文交流的发展促使出入境流动人口规模显著增长,老挝、越南、缅甸与中国的跨境流动人口造成中国广西、云南疟疾的广泛流行。中国推进的“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中外贸易的繁荣,中外人员流动不断增多,高速增长的流动人口为传染病跨境传播提供了重要载体,给重大传染病防控带来了不可预见的复杂性和多变性。
2003年的“非典型肺炎”(SARS)疫情的跨境传播,对中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等国家人们的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对旅游、交通、餐饮等产业造成严重的冲击。经贸与人文交流的发展促使出入境流动人口规模显著增长,老挝、越南、缅甸与中国的跨境流动人口造成中国广西、云南疟疾的广泛流行。中国推进的“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中外贸易的繁荣,中外人员流动不断增多,高速增长的流动人口为传染病跨境传播提供了重要载体,给重大传染病防控带来了不可预见的复杂性和多变性。
另外,核污染问题也是困扰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一个环境问题。2011年,日本发生福岛核电站泄漏事故。事故发生后,核污染产生的有害放射性物质扩散到日本东部及太平洋海域,随着海水运动扩散至中国东北部及韩国、朝鲜等国。另外,核污染气体借助大气运动,将污染物传输到更大的范围。日本核电站泄漏后一段时间内,东北亚国家和中国的台湾地区均检测出有害核辐射物,造成了甲状腺癌等健康问题。核事故还造成了区域内的人心惶惶,给东北亚各国的环境问题及合作带来新的难题和挑战。
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人员交流与经济发展引发的环境卫生问题越来越突出。传染病问题、空气污染问题、核污染问题等,给中国与周边国家带来了严重的环境压力。由于全球化时代的污染问题跨越了国家的行政边界,基于传统行政区域的环境治理模式已经难以有效应对新时期的环境问题。全球化的区域环境问题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命运紧紧连接在一起,中国与周边国家需以命运共同体为指引,通力协作,才能更好地解决环境问题。
四、构建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是应对经济危机的需要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蓬勃兴起,世界各国经济依存度日益提高。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迅猛发展,促使国际分工进一步飞跃,各国经济的相互联系更加广泛和深入。经济交织联系多一分,经济危机的联动性便会增一分。中国与周边各国地缘相邻、人文相通,经济上的相互影响和制约程度更加明显。中国与周边国家要协同发展,必然将区域各国视为整体中的一环。中国与周边国家联动发展不仅带来了机遇与繁荣,还带来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潜在威胁。区域联动发展既增加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经济发展的机会,又加剧了区域经济的无序和风险。自由化程度最高的金融领域,是自发性、投机性和风险最大的领域,近年来国际金融危机频频发生便是明证。习近平对此特别强调:“我们要注意防范风险叠加造成亚太经济金融大动荡,以社会政策托底经济政策,防止经济金融风险演化为政治社会问题。”
经济的跨国联动发展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区域国家在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利益同时,也承受着与日俱增的经济联动风险。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全面爆发,给亚洲国家带来了沉重灾难,使中国与周边国家切实感受到了区域经济危机的严重性。2008年,美国的“金融海啸”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中国与周边国家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解决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其思路显然不能是“反全球化”“非全球化”或“去全球化”等因噎废食的举措,而只能是在拥抱全球化的过程中,以加强国际经济合作与协调的方式加以解决。正如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二十国集团伦敦峰会上指出的那样:“这场国际金融危机是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与国相互依存日益紧密的大背景下发生的,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合作应对是正确抉择。”
以经济联动为特征的全球化时代,改变了人类的生存面貌。全球化促进了国际依存关系的全面深化,国家依凭地缘因素进行的互动更加频繁。全球化时代把国家的内部治理与全球治理结合在一起,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国际关系。中国秉承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以开放包容、平等互利的方式,增强与周边国家的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有利于中国与周边国家间经济发展的优势互补,形成了平等互惠、相互帮扶、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随着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在中国与周边国家落地生根,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将进一步深化,经济纽带将更加牢固。
在全球化时代,人类同住一个“地球村”,各国人民相互依存、休戚与共。中国与周边国家交往的增多,加速了商品、文化、人才的跨国界流动,也为恐怖问题、毒品犯罪、环境问题和经济危机等问题的跨境勾连埋下了隐患。全球化时代,跨境联动成为一种常态,国内与国际问题的边界变得模糊,呈现出国内问题国际化、国际问题国内化的发展趋向。习近平指出,“随着全球性挑战增多,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已是大势所趋。”“全球治理体制变革离不开理念的引领,全球治理规则体现更加公正合理的要求离不开对人类各种优秀文明成果的吸收。要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继续丰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
恐怖问题、跨境犯罪、环境问题和经济发展等问题,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越是面临全球性挑战,越要合作应对,共同变压力为动力、化危机为生机。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安全威胁,单打独斗不行,迷信武力更不行,合作安全、集体安全、共同安全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选择。” 中国作为负责任的新兴大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和有效的国际新制度。构建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回应了周边国家的普遍期待,顺应了新全球化时代的历史潮流,是中国基于人类共同利益贡献出的中国方案、中国智慧。
中国作为负责任的新兴大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和有效的国际新制度。构建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回应了周边国家的普遍期待,顺应了新全球化时代的历史潮流,是中国基于人类共同利益贡献出的中国方案、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