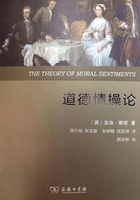
第三章 论由钦佩富人和大人物,轻视或怠慢穷人和小人物的这种倾向所引起的道德情操的败坏
钦佩或近于崇拜富人和大人物,轻视或至少是怠慢穷人和小人物的这种倾向,虽然为建立和维持等级差别和社会秩序所必需,但同时也是我们道德情操败坏的一个重要而又最普遍的原因。财富和地位经常得到应该只是智慧和美德才能引起的那种尊敬和钦佩;而那种只宜对罪恶和愚蠢表示的轻视,却经常极不适当地落到贫困和软弱头上。这历来是道德学家们所抱怨的。
我们渴望有好的名声和受人尊敬,害怕名声不好和遭人轻视。但是我们一来到这个世界,就很快发现智慧和美德并不是唯一受到尊敬的对象;罪恶和愚蠢也不是唯一受到轻视的对象。我们经常看到:富裕和有地位的人引起世人的高度尊敬,而具有智慧和美德的人却并非如此。我们还不断地看到:强者的罪恶和愚蠢较少受到人们的轻视,而无罪者的贫困和软弱却并非如此。受到、获得和享受人们的尊敬和钦佩,是野心和好胜心的主要目的。我们面前有两条同样能达到这个我们如此渴望的目的的道路:一条是学习知识和培养美德;另一条是取得财富和地位。我们的好胜心会表现为两种不同的品质:一种是目空一切的野心和毫无掩饰的贪婪;一种是谦逊有礼和公正正直。我们从中看到了两种不同的榜样和形象,据此可以形成自己的品质和行为:一种在外表上华而不实和光彩夺目;另一种在外表上颇为合式和异常美丽;前者促使每一只飘忽不定的眼睛去注意它;后者除了非常认真、仔细的观察者之外,几乎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他们主要是有知识和美德的人,是社会精英,虽然人数恐怕很少,但却是真正、坚定地钦佩智慧和美德的人。大部分人都是财富和显贵的钦佩者和崇拜者,并且看来颇为离奇的是,他们往往是不具偏见的钦佩者和崇拜者。
毫无疑问,我们对智慧和美德怀有的尊敬不同于我们对财富和显贵们所抱有的尊敬;对此加以区分并不需要极好的识别能力。但是,尽管存在这种不同,那些情感还是具有某种非常值得注意的相似之处。它们在某些特征上无疑是不同的,但是在通常的外部表现上看来几乎相同,因而粗心的观察者非常容易将两者混淆起来。
在同等程度的优点方面,几乎所有的人对富人和大人物的尊敬都超过对穷人和小人物的尊敬。绝大部分人对前者的傲慢和自负的钦佩甚于对后者的真诚和可靠的钦佩。或许,撇开优点和美德,说值得我们尊敬的仅仅是财富和地位,这几乎是对高尚的道德甚至是对美好的语言的一种亵渎。然而,我们必须承认:财富和地位几乎是不断地获得人们的尊敬;因此,在某些情况下它们会被人们当作表示尊敬的自然对象。毫无疑问,罪恶和愚蠢会大大贬损那些高贵的地位。但是,它们必须很大才能起这样的作用。上流社会人士的放荡行为遭到的轻视和厌恶比小人物的同样行动所遭到的小得多。后者对有节制的、合乎礼仪的规矩的仅仅一次违犯,同前者对这种规矩的经常的、公开的蔑视相比,通常更加遭人愤恨。
很幸运,在中等和低等的阶层中,取得美德的道路和取得财富(这种财富至少是这些阶层的人们能够合理地期望得到的)的道路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极其相近的。在所有的中等和低等的职业里,真正的、扎实的能力加上谨慎的、正直的、坚定而有节制的行为,大多会取得成功。有时,这种能力甚至会在行为不端之处取得成功。然而,习以为常的厚颜无耻、不讲道义、怯懦软弱、或放荡不检,总会损害、有时彻底损毁卓越的职业才能。此外,低等和中等阶层的人们,其地位从来不会重要得超越法律。法律通常必然能吓住他们,使他们至少对更为重要的公正法则表示某种尊重。这种人的成功也几乎总是依赖邻人和同他们地位相等的人的支持和好评;他们的行为如果不那么端正,就很少能有所获。因此,“诚实是最好的策略”这句有益的古老谚语,在这种情况下差不多总是全然适用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一般都希望人们具有一种令人瞩目的美德;就一些良好的社会道德而言,这些幸好是绝大部分人的情况。
不幸的是,在较高的阶层中情况往往并非如此。在宫廷里,在大人物的客厅里,成功和提升并不依靠博学多才、见闻广博的同自己地位相等的人的尊敬,而是依靠无知、专横和傲慢的上司们的怪诞、愚蠢的偏心;阿谀奉承和虚伪欺诈也经常比美德和才能更有用。在这种社会里,取悦于他人的本领比有用之才更受重视。在平静和安定的时代,当骚乱尚未临近时,君主或大人物只想消遣娱乐,甚至会认为他没有理由为别人服务,或者认为那些供他消遣娱乐的人足以为他效劳。上流社会的人认为那种傲慢和愚蠢的行为所表现的外表风度、浅薄的才能,同一个战士、一位政治家、一名哲学家或者一名议员的真正的男子汉式的美德相比,通常可以得到更多的赞扬。一切伟大的、令人尊敬的美德、一切既适用于市政议会和国会也适用于村野的美德,都受到了那些粗野、可鄙的马屁精的极端蔑视和嘲笑。这些马屁精一般都充斥于这种风气败坏的社会之中。当苏利公爵 被路易十三召去就某一重大的突然事件发表意见时,看到皇上恩宠的朝臣们交头接耳地嘲笑他那过时的打扮,这位老军人兼政治家说:“当陛下的父亲不论何时让我荣幸地同他一起商量国家大事时,总是吩咐这种宫廷丑角退入前厅。”
被路易十三召去就某一重大的突然事件发表意见时,看到皇上恩宠的朝臣们交头接耳地嘲笑他那过时的打扮,这位老军人兼政治家说:“当陛下的父亲不论何时让我荣幸地同他一起商量国家大事时,总是吩咐这种宫廷丑角退入前厅。”
正是由于我们钦佩富人和大人物、从而加以模仿的倾向,使得他们能够树立或导致所谓时髦的风尚。他们的衣饰成了时髦的衣饰;他们交谈时所用的语言成了一种时髦的语调;他们的举止风度成了一种时髦的仪态。甚至他们的罪恶和愚蠢也成了时髦的东西。大部分人以模仿这种品质和具有类似的品质为荣,而正是这种品质玷污和贬低了他们自己。爱虚荣的人经常显示出一种时髦的放荡的风度,他们心里不一定赞同这种风度,但或许他们并不真正为此感到内疚。他们渴望由于连他们自己也认为不值得称赞的什么东西而受到称赞,并为一些美德受到冷遇而感到羞愧,这些美德他们有时也会偷偷地实行并对它们怀有某种程度的真诚的敬意。正如在宗教和美德问题上存在伪君子一样,在财富和地位问题上也存在伪君子;恰如一个奸诈之徒用某种方式来伪装自己一样,一个爱好虚荣的人也善于用别的方式给人一种假象。他用地位比自己高的人用的那种马车和豪华的生活方式来装扮自己,没有想到任何地位比他高的人所值得称道的地方,来自同他的地位和财富相称的一切美德和礼仪,这种地位和财富既需要,也能够充裕地维持这种开支。许多穷人以被人认为富裕为荣,而没有考虑这种名声加给自己的责任(如果可以用如此庄严的名词来称呼这种愚行的话),那样,他们不久一定会沦为乞丐,使自己的处境比原先更加不如他们所钦佩和模仿的人的处境。
为了获得这种令人羡慕的境遇,追求财富的人们时常放弃通往美德的道路。不幸的是,通往美德的道路和通往财富的道路二者的方向有时截然相反。但是,具有野心的人自以为,在他追求的那个优越的处境里,他会有很多办法来博得人们对他的钦佩和尊敬,并能使自己的行为彬彬有礼,风度优雅;他未来的那些行为给他带来的荣誉,会完全掩盖或使人们忘却他为获得晋升而采用的各种邪恶手段。在许多政府里,最高职位的候选人们都凌驾于法律之上;因而,如果他们能达到自己的野心所确定的目标,他们就不怕因自己为获得最高职位而采用的手段而受到指责。所以,他们不仅常常通过欺诈和撒谎、通过拙劣卑鄙的阴谋和结党营私的伎俩,而且有时通过穷凶极恶的罪行、通过谋杀和行刺、通过叛乱和内战,竭力排挤、清除那些反对或妨碍他们获得高位的人。他们的失败往往多于成功;通常除因其犯下的罪行而得到可耻的惩罚之外一无所获。虽然他们应该为得到自己梦寐以求的地位而感到十分幸运,但是他们对其所期待的幸福总是极为失望。充满野心的人真正追求的总是这种或那种荣誉(虽然往往是一种已被极大地曲解的荣誉),而不是舒适和快乐。不过,在他自己和他人看来,他提升后的地位所带来的荣誉,会由于为实现这种提升而采用的卑鄙恶劣的手段而受到玷污和亵渎。虽然通过挥霍各种大量的费用,通过恣意放纵各种放荡的娱乐(这是堕落分子可怜的但经常采用的消遣方法),通过繁忙的公务,通过波澜壮阔和令人炫目的战争,他会尽力在自己和别人的记忆中冲淡对自己所作所为的回忆,但是这种回忆必然仍会纠缠不休。他徒劳无益地求助于那使人忘却过去的隐秘的力量。他一回想自己的所作所为,记忆就会告诉他,别人一定也记得这些事情。在一切非常浮华的盛大仪式之中,在从有地位者和有学问者那里收买来的那种令人恶心的阿谀奉承之中,在平民百姓颇为天真然而也颇为愚蠢的欢呼声中,在一切征服和战争胜利后的骄傲和得意之中,羞耻和悔恨这种猛烈报复仍然隐秘地纠缠着他;并且,当各方面的荣誉来到他身上时,他在自己的想象中看到丑恶的名声紧紧地纠缠着,它们每时每刻都会从身后向他袭来。即使伟大的恺撒,虽然气度不凡地解散了他的卫队,但也不能消除自己的猜疑。对法赛利亚的回忆仍然萦绕心头,无法甩脱。当他在元老院的请求下,宽大地赦免了马尔塞鲁斯的时候,他告诉元老院说,他不是不知道正在实施的杀害他的阴谋,但是因为他已享足天年和荣誉,所以他将心满意足地死去,并因此藐视一切阴谋。或许,他已享足了天年,但是,如果他希望得到人们的好感,希望把人们视为朋友,但却受到人们极端的仇视,如果他希望得到真正的荣誉,希望享有在同他地位相等的人的尊敬和爱戴之中所能得到的一切幸福,那么,他无疑是活得太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