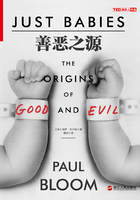
拥有道德不能缺了同情
虽然“同情”和“道德”并不相同,而且有时二者还会发生冲突,但是“同情”对“道德”来说仍然必不可少。如果我们对他人漠不关心,我们就不可能拥有道德。
从我们降临人世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就和他人产生了联系。“没有哪个婴儿是一座孤岛” ,就算是刚刚出生的婴儿,也会对他人的表情作出反应:如果一位实验人员冲婴儿吐舌头,婴儿很可能会试图模仿。但是他从来没有看过镜子,所以他必然从本能上知道,这个大人的舌头就对应着自己嘴里的那个东西——虽然他可能从来没有亲眼见过。这类模仿行为的目的很可能是让婴儿和周围成年人建立起某种联系,把他们的情感维系在一起。事实上,父母和婴儿经常在不经意间模仿对方的表情。
,就算是刚刚出生的婴儿,也会对他人的表情作出反应:如果一位实验人员冲婴儿吐舌头,婴儿很可能会试图模仿。但是他从来没有看过镜子,所以他必然从本能上知道,这个大人的舌头就对应着自己嘴里的那个东西——虽然他可能从来没有亲眼见过。这类模仿行为的目的很可能是让婴儿和周围成年人建立起某种联系,把他们的情感维系在一起。事实上,父母和婴儿经常在不经意间模仿对方的表情。
婴儿也会对他人的痛苦作出反应。还记得小威廉在6个月大时就表现出了同情之意吗?当保姆假装哭泣的时候,他也在“脸上流露出明显的忧伤”。就算婴儿刚刚出生几天,他们也会因为他人的哭声而感到难过,往往自己也会跟着哭起来。他们并不是对哭声或噪声刺激盲目作出反应。因为研究发现,与听到自己的哭声相比,婴儿在听到其他婴儿的哭声之后往往会哭得更加厉害;而且就算他们听到由电脑合成的音量相同的噪声,或者黑猩猩幼崽的哭声,他们也不会哭得这么厉害。
其他生物如果发觉自己的同类正在承受痛苦,它们也会感到难过。如果恒河猴发现一旦它们拉动那个能带来食物的操纵杆,就会给另一只恒河猴带来痛苦的电击,那么它们就算饥肠辘辘也不愿意这样做。老鼠会向同类伸出援手,按压操纵钮把困在半空中的老鼠救下来,或者把困在装满水的水箱里的老鼠放出去;它们也和恒河猴一样,如果发现按压按钮会给另一只老鼠带来电击,即使这样做会为自己带来食物,它们也不会继续下去。
这类行为很可能反映出了我们的同情之心。但是我们也能找到一个更消极的解释:恒河猴和老鼠(可能还有人类)进化出了发现他人痛苦的能力,但没有进化出对痛苦个体的真正关切。也就是说,动物可能会产生共情,但不会产生同情。
我们在观察婴儿和幼儿的行为时发现了更多东西。面对他人的痛苦,他们并没有转身离去,而是试图通过自己的行动让那个人心情变好。发展生物学家在很久以前就观察到,年仅一岁的婴儿会通过轻拍安抚痛苦之人。心理学家卡罗琳·赞恩–韦克斯勒(Carolyn Zahn-Waxler)和她的同事发现,如果幼儿从自己周围的人的举动之中发现他们似乎十分疼痛(比如母亲撞到膝盖,或者实验人员的手指被夹板夹住),他们常会作出安抚行为。而且安抚行为也存在性别差异,女孩比男孩更倾向于安抚他人。这种性别差异又与大量实验研究的结果相吻合,许多研究证明,女性一般来说怀有更大的共情和同情之心。你还可以在其他灵长类动物身上观察到类似的安抚行为。根据灵长类动物学家弗兰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的说法,黑猩猩会张开手臂环抱受到攻击的同类,轻拍它或者为它清理毛发——但是猴子却不会作出类似行为。
不过婴儿和幼儿在安抚他人方面作出的尝试十分有限,频率也并不太高。研究发现,幼儿抚慰他人的频率要低于更年长的儿童,而后者又低于成年人。有时幼儿在看到他人承受痛苦时自己也会变得很悲伤,然后他们就会回过头来安抚自己,而不是那个真正承受痛苦的人。由共情引发的痛苦会令人感到难过,但有时难过之意实在太过强烈,会让他们自己情绪崩溃。对于老鼠来说,情况也是如此。在一项实验中,老鼠可以通过按压某个按钮来阻止另一只老鼠遭受痛苦的电击。但是很多老鼠都不敢去按那个按钮,而是“缩回到鼠笼最远处的角落里,然后蹲在那儿一动不动,远离那个因疼痛而尖叫不断、因电击而跳动不停的同类”。
幼儿对他人痛苦的反应有时也出于利己私心。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自己也希望得到同样的待遇。比如心理学家马丁·霍夫曼(Martin Hoffman)曾经写道,一个14个月大的婴儿带着正在哭泣的同伴去找自己的母亲,而不是那个哭泣孩子的母亲。当时霍夫曼认为,幼儿之所以会“搞混”,是因为他们的认知发育还不够成熟,无法从他人的角度思考问题。但事实上,在面对他人的痛苦时,任何年龄段的人都有可能从自己的角度想问题。有一天,我和妻子并排坐在一间餐厅里用餐。妻子提到她口干舌燥,于是我礼貌地把自己的啤酒递给她。但她只是盯着我看。过了片刻我才意识到,她痛恨啤酒,而我热爱啤酒。